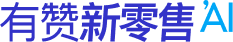1
“Stay hungry, stay foolish.”
第一次听到这句话是将近十年前第一次看 Steve 的 Stanford Commencement Speech。当时的我拿着当时父母朋友刚送的——也是苹果的刚面世的第一代 iPad Mini,反复打量、摩挲着这台离我如此遥远同时也是人生里的第一台数码产品。
那时苹果公司的名号早已响彻世界,在无数少年的心里,这个被咬掉了一个小角的 logo 意味着高端的档次,意味着脱离那个从桌面电脑向移动设备转移的混乱且无序的时期的一种更简单和更个性的自我标榜,也意味着隐隐约约脑袋上方好像有一个无所不能的“神”在安抚着这些年轻躁动的心。
那是一种极其神奇的力量,到现在都会觉得冥冥之中有些许不可思议。跟现在一样,苹果设备的外包装并不好看。但每次从这个手感略微廉价的白色盒子里拿出这个磨砂材质的银白色的物件,对我来说都是一个神圣庄严的过程,生怕会有不光彩的灰尘沾染上了它。
另一方面,互联网本是一个让少年无法拒绝的大染缸,它是我的百科全书,是我的思想启蒙的来源,但就像有一个人拎着一把戒尺时刻顶着我的脑袋,它在我的日常生活中却多多少少起着一些约束作用。一种无形的戒律萦绕在我身旁。
“这是上帝派给我的礼物,警示我面对诱惑要严于律己吗”,那时候受林书豪的影响还在钻研《圣经》的我想道。
我迫切地想要知道那个隐隐约约笼罩着自己的“神”到底是谁。这便是我与 Steve 和 Stay hungry stay foolish 这句话的第一次碰面。窗边的我挺直着身体,看着眼前这个秃顶的中年男人时不时低下头看他眼前的讲稿。我心里略有些失落,“原来神长这样子”。不过仔细一想,发现原来之前知道他,知道他前段时间刚去世,新闻铺天盖地都是他的报道,还有更早些时候有一个很白的黑人也一起去世了。我心里顿时充满了不可言喻的尊重,Steve 在 Commencement Speech 上最后那句有节奏感的掷地有声的 stay hungry stay foolish,配合他习惯性的望向远方的眼神,从那时开始成就了我心里最庄重、最装的谢幕方式。
十年前,Steve 永远地谢幕了。他作为科技之神的那种隐约的能量在我得知他去世之后逐渐开始散退。当时的我颇有预见性地认为会有新的人来继承科技之神的位置,到那时这种能量也会重新在自己身上被 pick up 起来。
十年之后,科技之神的确换了,但换的不是人,而是一个比人更聪明的东西。
2
PC 时代的互联网跟人类的关系更像是工具和使用者的关系,工具的价值依附于使用者而存在,这种依附性使得互联网的作用常常被限制在那个厚重的主机外壳内。而跟十年前不同的是,如今的互联网跟人类更像是主人跟狗这种短期若即若离而长期固定的关系,狗会时而走得慢时而走得快,甚至会想要挣脱主人的拴狗绳,但始终会 converge 回到主人身边。而人就是那条狗,互联网就是狗的主人。
算法已经成为了那个不得不顶礼膜拜的科技之神。
互联网的高度渗透之下,人早已不再是人,甚至连狗都不是,而是由无数数据描述和勾勒出来的虚拟人。这个虚拟人甚至比人的社会人格更加真实,那些经过修饰的社会人格之下的任何一点小动作都会被捕捉,这种人身的暴露无疑是全方位的。而算法的一大特征,或者说此时我们主要谈论的推荐算法的特征,便是高度个性化的自我强化。简单来说,人们在互联网上的行为本身会成为历史数据集,喂给算法后便会训练算法根据人们之前的偏好来进行新的分发和推荐。
结果就是,人们会越来越多地看到、听到、认识到那些本来就喜欢或者想要知道的信息,而这些信息的反面因为被认为是与虚拟人的偏好无关联的或者被认为是相对更难以在更广范围传播的,而更加不会被主动地呈现在人们眼前。
算法的这一面,其实是一种对“真实性”的刻意隐瞒。幼儿之所以成长为人,这种成长极大程度上来源于对于世界和事物本就有的复杂性 complexity 的还原,以及对于这种复杂性的解构能力。在相对单一或关联性较强的信息持续渗透下,人们缺乏对于事物的复杂性的理解、或者对复杂性的理解能力逐渐消失的现象已经越来越显而易见。
这种现象有两个特征。
一是主观意识上的 complexity 的坍缩。
人们意识中的 complexity 会坍缩为二元对立的状态,人们对于复杂性的理解逐渐从多层次多元的角度演变为对于事物只持有正反两面的理解,甚至只有一面。简单来说,人们对于事物的认知会逐渐被 shape 成为非黑即白的二元对立状态,且不容许与自己对立的另一方的声音甚至第三种声音出现。这样的例子在近年有很多,大家心里一想就知道,不管是在意识形态、文化、科技、政治、教育各个方面,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其他西方国家。
但本质来看,这就是人性,简单化的对立化的思考是一种植根于人内心本性的潜意识,因为这是最简单也是最偷懒的思考方式。同时,情绪也会更多地参与进来,最终会固执地沉溺在为自己的情绪而非观点抵抗。因此这也是算法聪明的地方所在。它真正从它的底层逻辑做到了顺应人性和放大人性,让人非常自然地沉浸在被与生俱来的人性所支配的状态中。
都说顺应人性的生意才是好生意,从这一点来说,这些可都是上等的好生意。
但这对人的创造力,却是无比致命的。算法不能理解艺术,就像人无法理解宇宙。这是区分算法和人的重要特点,人的创造性可以赋予事物以艺术价值,就像 Steve 之于苹果,这是无法被人之外的力量所超越的。
包含一种声音的艺术只能算作洗脑,而容纳了两种声音的艺术也只是宣传。
对于复杂性的解构能力消失的第二个特征,则跟所谓的廉价情感有关。
举一个例子。最近这些年好像大家不再怎么讨论华语流行音乐了。这几年似乎没出现过多少大家到现在依然能记住并反复听的华语流行音乐作品。翻开自己最爱的流行音乐歌手,来来去去似乎都是周杰伦、王力宏之类的这种巅峰出现在十几二十年前的歌手。
但另一方面,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始终被各种新音乐笼罩。借助算法,新音乐作品在短时间即可完成破圈,被无数人在无意间哼唱,但遗忘速度也是出奇地快。这些音乐作品的生命周期通常不到一个月。一个月之后,这些上耳但毫无记忆点的哼唱就像昙花一样会被人们彻底遗忘。
试问,三年前的同类型音乐,有哪些你现在还在听呢?作为音乐人的我,我的答案是没有。而除此之外的其他类型的音乐,包括十年前仍流行的网络音乐,其中绝大部分在如今都无法坐上国民级音乐的位置,其中也包括不少那些在十几二十年前仍是巅峰的流行歌手的作品。
最近有人做过统计,某视频平台近三年所有前十名歌曲的和声编排方式,没有几十种,也没有十种,而是只有三种。他们分别是:卡农组、6415 组和 4536 组。
正如视频内容,算法分发音乐所采纳的数据点有很多,但其中最重要的无疑就是那开头几秒最多十秒的数据表现。这样高度一致的和声编排,很可能是音乐制作公司反推算法得出来的最佳编排结果。当然,二十年前的流行音乐许多也采取类似的编排方式,但在具体的旋律、器乐选择、风格特色上,相比之下都有着更多的变化。而这些变化对于歌曲传播广度的作用,在如今是微不足道的。
是因为人的品味变了吗?
其实不然。与二十年前不同,如今音乐的传播渠道在互联网这个边际成本极低的载体上被打通,不同人群之间的传播壁垒理论上并不存在;加上算法在其中扮演的核心分发的角色,一首作品的能传播多广的命运基本由开头或者副歌部分那几秒十几秒决定。
这个逻辑的荒谬之处就好比同样是艺术品的酒,判断它好坏的标准不是它入口后再入食道的体验感,而变成了比如直接看它的颜色,颜色越抓人,酒的价值就越高。这样的逻辑会迫使 music producer 将音乐做得尽可能广泛而非深入、上脑而非独特,最终满足的是人们的廉价情感。
而所谓的廉价情感,指的就是那些多了不浪费、少了不珍惜的情绪感受。这些情绪感受来得快去得也快,由于其自身大量和泛滥而天然地无法被人们所珍惜和记忆。
二十年前的春晚节目,可是能被做成 CD 在车上当唱片反复听反复念叨的。陈佩斯的春晚系列、赵本山的卖拐三部曲、大兵的方言相声,我跟不少长辈都能像歌一样完整地哼出来。现在我把它们称之为“挠痒痒”艺术,唯一的作用就是挠个痒痒,不痛也不痒。当这些作品一再远离那些真正重要的议题时,创作者们也只能一再东拼西凑般地强行制造对立来满足“冲突感”——这一艺术最核心的元素。
我想,创作者本身也一定很难受,但也一定会感到幸运,因为作品最终避开了那些真正重要的议题而只冒犯了观众的一点无足轻重的皮毛而已,没犯什么“大错”。
这或许也跟上面提到的第一点——复杂性的坍缩有关。人们对于多样性的抵触,反过来也会使得艺术作品不再涉险触碰深度,而只能漂浮在浅滩。
3
叠加这两点特征,我们便可以看得到一种正在成型的趋势——一种社会共识上的割裂。
这是日本东京练马区不知名的一隅。当时在附近参观完当地的垃圾处理中心后,便晃晃悠悠地游荡到这。正值寒冬,小河上整齐的樱花树只剩下张牙舞爪的枝桠。仔细观察,河道的两边都是平整且统一的居民区,而河道相对的则是两个几近垂直的岸边,上面无法附着什么东西。若没有中间的桥在两端相连,河道两边颇有一种针锋相对即将开战的阵势。
社会共识也是如此。对于复杂的解构能力变弱,会逐渐使得社会共识的聚焦点出现分裂的发展状态。一方面,充斥廉价情感的“挠痒痒”艺术让人们在最广泛的层面上形成共识、共鸣和某种政治正确;另一方面,一旦触角试探到更深入的价值观、意识形态、观念、文化等等方面,社会共识便会显现出相当割裂的姿态。社会共识在两个层面形成巨大分野。
讽刺的是,现在看来算法反而是那个最有可能管理社会共识的工具。这无疑是一种人文和艺术性的衰退。但它也意味着更高级更有效率的社会治理。当算法上升至国家治理,它在治理上的高效性会更充分地被体现出来,这将会是一种高度的中心化的集权治理体系。
遥想当年,万维网之父 Berners-Lee 创造了万维网上的第一个网站和第一个伺服器。互联网是一个充满了理想主义情怀的产物,那是一个真正的去中心化的世界,给这个信息渠道被垄断的世界带来了新的曙光。它的核心作用在于平权,在于给所有人 – 无论背景和肤色都提供一个能自由交流自主 speak up 的媒介,人们能够畅所欲言和自由地交换信息。
恰恰相反的是,三十年后的今天,互联网和算法之下的世界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走向中心化,马太效应在过去二十年太过于明显。人们变得更加对立而非包容,公司和组织逐渐强者恒强弱者恒弱。这是一种莫大的讽刺。
顺嘴说一句,web 2.0 走向 3.0 的过程中的一大特点其实是重现这种互联网的初衷——即去中心化的平权效应。区块链的诞生或许是完成这个进化的重要技术。区块链中同样由一种特定算法——smart contract 智能合约所自动运行的分布式治理的体系,本质上是对互联网信息验证、传播和保存技术的一种范式上的转变和提升。
但从中本聪的论文开始算起,虽然区块链已经野蛮生长了十几年,中间经历的大牛大熊和被无限放大的羊群效应,几乎将优秀的人才和资方都吸引到了赚钱效应更高的数字货币金融和围绕其打造的各类收益体系中,以获取极高的财务回报。这也使得区块链在治理上的优越性被喧宾夺主,无法实现真正的破圈。三十年前互联网的诞生在社会治理层面本有机会将现代社会的治理体系从民主引导至共和,但现在来看它的作用已被完全弱化。是否可以 takeover 这个角色,就让时间给我们答案吧。
下面摘抄了一段来自以太坊创始人 Vitalik Buterin——人称 V 神的 2020 年总结性文章 “Endnotes on 2020: Crypto and Beyond”中的一部分,讲的正是跟治理相关的话题,供大家参考。
Many online platforms serving wide groups of people need governance, to decide on features, content moderation policies or other challenges important to their user community, though there too, the user community rarely maps cleanly to anything but itself. How is it fair for the US government to govern Twitter, when Twitter is often a platform for public debates between US politicians and representatives of its geopolitical rivals? But clearly, governance challenges exist – and so we need more creative solutions.
同样颇为讽刺的是,在 Steve 说出这句 stay hungry stay foolish 之前,他曾提到过这句话来源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一本杂志:Whole Earth Catalog。这本在垮掉的一代向嬉皮士时代转移的时期中出版的杂志,无数次地在杂志里向主流文化提出过挑战,甚至它的定位就是一本 counterculture 的反主流文化杂志。它是个性的象征,也是反抗世俗追求自我的拓荒者。Stay hungry stay foolish这句话最经典的中文翻译是:求知若饥,虚心若愚。
但在 Steve 辞世的十年后,替代了 Steve 的新的科技之神——算法,却使人们加速走向这本杂志和这句话的对立面。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神仙湖畔(ID:shenxianhupan),作者:nw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