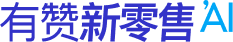每次出国旅行,我都希望能掌握几句当地语言,流利与否是另一回事。我是语言老师的儿子,小时候学过法语。20来岁在墨西哥漫游时,我学会了西班牙语,但在那以后,我就忙碌起来。尽管终生渴望学意大利语,不过人到中年,我还是只会“Per favore”和“Grazie”。最近,米兰附近的一个会议邀请我参加,这让我又想冒险尝试。但每天都被工作期限和家庭义务塞得满满的,我没一丁点时间上夜校,或通过APP在家学。我猜,也许我能通过睡眠中听录音来掌握这门“美丽的语言”(la bella lingua)。
近一个世纪前,“睡眠学习法”的热潮席卷了整个工业化社会,直到神经科学家确定该方法在生理上并不可实现,热潮方才褪去。然而今天,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当年那些神经科学家们或许错了。睡眠学习法似乎正走向复兴,科学依据比其前身要坚实得多。通过对睡眠进行一些工程性的调整或修正,我们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大脑每晚的离线时间,为吸收信息争取宝贵时间。经过许多夜晚,我们可以极大扩展知识和技能储备,甚或治疗顽固瘾癖和心理创伤。
但这一切都指向一个令人不安的问题:我们该欢迎还是害怕这种前景?如果我们利用睡眠来自我提升,我们是否会失去某些自身的本质?
由来已久的睡眠学习法
人类可以在睡眠中学习的观点至少可追溯到《圣经》时代,上帝让雅各布在梦中看到天使爬上天国之梯,从而瞥见自身命运。但从这个概念中赚钱的第一人是阿洛伊斯·本杰明·萨利格(Alois Benjamin Saliger),一位生于捷克、居于纽约的商人兼发明家(据时人描述,他“高个子,身材瘦削,薄嘴唇,有一双锐利的眼睛和宽阔前额”),于1932年获“心理电话”专利。
这种留声机装有一个重复装置和一个小喇叭,可以放在睡眠者的床边,以耳语的音量重复播放口语录音。和它一起销售的还有一些唱片,唱片名包括《繁荣》《灵感》《正常体重》和《交合》。
萨利格在最后一张唱片中庄严吟诵:“我渴望一个理想的伴侣,我散发着爱的光芒,我拥有迷人且有魅力的个性。我有强烈的性吸引力。”如果这台机器的功能正如广告所言,那么用户醒来时就会充满无可阻挡的自信,准备大步流星地征服被其拣选的领地。
“心理电话”的运作前提是,人们在睡眠状态下和催眠状态下一样易受暗示,阿尔多斯·赫胥黎(Aldous Huxley)在他的反乌托邦小说《美丽新世界》中就曾采用了这个未经证实的理论。小说里,录音讯息用以训练熟睡的儿童,让他们形成一种缺乏人性、道德和情感的未来社会价值观,赫胥黎将其称为“睡眠教学法”(hypnopaedia)。书中,一位自豪的官员说,这种新方法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道德教化和社会化力量”。
尽管睡眠教学法从未在现实世界中用于大规模灌输教育,但它逐渐被广泛当成工具,用来传授新技能或改变不良行为。科学研究似乎表明它是有效的。
在一项研究中,一群熟睡的人听到了一串中文词汇及英文翻译的录音,第二天,他们在理解测试中的得分明显高于对照组。在另一项研究中,研究者对20名有咬指甲习惯的男孩,每晚播放300次短语“我的指甲尝起来苦得要命”,播放了54晚。试验结束时,据报道,40%的男孩克服了他们的恶习。这种方法在苏联变得特别流行,据说整个村庄的人都在打盹时学外语。
这种观念在上世纪50年代迎来反转,那时候科学家们开始使用脑电图(EEG)技术。有了这项技术,他们终于可以确定受试者是否真的睡着了,而不是昏昏欲睡或仅在闭眼休息。
兰德公司的研究人员威廉·埃蒙斯(William Emmons)和查尔斯·西蒙(Charles Simon)向一些男性反复播放10个单词的列表,这些男性的脑电图显示当时他们脑中没有α波(这是睡眠的可靠指标)。结果,他们在清醒后记忆测试中的表现,并不比随机情况好。其他脑电图监测试验也得出了相似的结果。科学共识很快达成:熟睡中的大脑无法接收外界信息*,睡眠教学法被归为江湖医术的范畴。
*译者注:最近发表于《自然-神经科学》的研究得出了相反的结论。
现在,钟摆又开始摆动了。尽管还没有切实有效的方法存在(除了网上骗子们的声称),但最近的研究表明,睡眠教学法原则上是可行的。如果能克服某些技术难题,它将真正开辟一个“美丽新世界”。
人们对睡眠学习法产生新的兴趣,是因为对“一动不动地躺在床上流口水时,我们的大脑在做什么”有了更深入的了解。长期以来的实验表明,比起前一晚没睡好的人,一晚安眠的人能更好地回忆起前一天所学的知识。但这是为什么呢?
睡眠中学习为何可能
有一种理论认为,大脑在以快速眼动(REM)为特征的梦中,演习前一个白天的新信息。然而,实验室研究最终否定了这一观点。到了上世纪90年代中期,数据显示了另一种观点:记忆主要是在被称为慢波睡眠(SWS)的深层无梦睡眠阶段演习的。(因为大脑脑电活动在高峰和低谷之间从容地循环,所以称为“慢波睡眠”。)
研究人员发现,在慢波睡眠阶段,大鼠海马中特化的“位置细胞”会重放白天学会跑的迷宫路线。其后的研究表明,人类也以非常相似的方式重现新记忆。海马会作为记忆的临时仓库,直到这些记忆在大脑皮层(语言、感知觉和思维所在)形成生成较慢但更永久的连接。
随着“熟睡中的大脑为消化白天学习的内容做了多少工作”逐渐变得清晰,“熟睡中学习”的概念也就似乎不那么牵强了。
1996年,日本研究人员通过诱发心理学家所谓的条件反射——将两种刺激联系起来,使重复第二种刺激触发通常与第一种刺激相关的反应——对睡眠学习法的基本形式进行了测试。他们对五名睡眠者的腿部进行了轻微电击,同时播放了一种声音信号;醒来后,被试单独听到这个声音信号时,出现心跳加快。研究证明,熟睡中的被试至少下意识地回忆起了这一声音信号。
2007年,由德国吕贝克大学医学心理学家詹·伯恩(Jan Born)领导的研究小组,利用嗅觉线索触发了完全有意识的记忆(陈述性记忆)。他们首先在被试记忆电脑屏幕上的物体位置时,将玫瑰花的气味送入受试者的鼻孔。然后,部分被试在慢波睡眠期间再次接触到这种香味。当这部分被试醒来时,他们回忆物体位置的准确率,比睡眠时未接触香味的对照组高出15%。
在随后的实验中,芝加哥西北大学的神经科学家肯·帕勒(Ken Paller)教被试在键盘上演奏一段简短的旋律。然后,当被试小睡时,对他们中的一半重复播放这段旋律。醒来后,这一组被试弹奏该旋律的错误率低于安静睡觉的那一组人。
另一项研究与我的语言学探索直接相关:在瑞士国家科学基金会,被试在白天学习荷兰语单词,晚上在慢波睡眠中重放这些单词后证明,他们能够更好地回忆和翻译这些单词。这些音乐和语言试验表明,听觉线索可以直接触发特定任务的记忆演习——完全不需要条件关联。
熟睡时也能学习新知识?
总之,这些研究近乎证明了睡眠学习法的概念。但有一点是缺失的:所有实验涉及的技能或信息都是在清醒时首次学习的。为了证明睡眠教学法的作用,科学家必须向熟睡中的被试教授新知识。
2015年3月,研究人员在《自然-神经科学》上报道他们已做到了。由巴黎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的神经生物学家卡里姆·本切纳内(Karim Benchenane)领导的研究小组,首先在小鼠大脑中植入电极,记录它们在一米宽的圆形平台上找路时,位置细胞的激活情况。
研究人员为每只小鼠选择一个位置细胞,然后等待它在睡眠中重新激活。在那时,他们用低压电流刺激小鼠大脑的奖励中枢,创造强烈的快感。当小鼠醒来时,它们会冲向与位置细胞相关的位置,在那里逗留,显然是在期待另一个奖励。科学家们制造了一种虚假记忆,改变了动物的行为方式,而这些行为方式并不是之前清醒时的经验所导致的。
de Lavilléon, Gaetan et al. “Explicit memory creation during sleep demonstrates a causal role of place cells in navigation.” Nature neuroscience vol. 18,4 (2015): 493-5. doi:10.1038/nn.3970
本切纳内的研究采用正强化的方法对被试小鼠进行训练。与此同时,以色列魏兹曼科学研究所的神经科学家们对人类尼古丁成瘾者采取了相反的方法,在慢波睡眠期间使他们暴露在香烟和臭鸡蛋(或臭鱼)的气味中。得益于这种厌恶性条件反射,参与者在接下来的一周里减少了30%的吸烟量。
而在美国西北大学,神经学博士后凯瑟琳娜·豪纳(Katherina Hauner)设计了一种在慢波睡眠过程中消除负面关联的方法。首先,她向志愿者展示人脸图像,同时给予不愉快的电击;与此同时,她让志愿者暴露在薄荷、柠檬或松树的气味中。被试很快就学会了将人脸与疼痛联系起来。
然后,在他们睡觉时,豪纳让他们单独接触这些气味。起初,他们的反应是恐惧(通过皮肤上的微量汗液测量得出),但这种反应随着气味重复出现而减弱。当被试醒来时,他们看到那些面孔时的焦虑也随之减轻。
不难看出,这种技术可以带来多么大的改变。当我在芝加哥给帕勒打电话时,他说:“我们正处于试图弄清‘沉睡的大脑能做什么’的最前沿。在短期内,我们可能会利用睡眠中已经发生的处理过程来改善学习。”升级后的“心理电话”可以设计为在慢波睡眠时提供提示,也许能帮助学生更快地掌握一门学科,但白天的学习仍然是必要的。该设备可与搭载经颅电刺激的头带配对使用,经颅电刺激在特定频率下可加深慢波睡眠。“豪华套餐”中还可包括一台香氛机,以增强整体效果。
睡眠学习法可用于治疗,用对相同事件不太激烈的回忆取代创伤记忆。这可能需要药物来撬开神经闸门,让“超级心理电话”将内容直接输送到海马。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科学家们最近发明了一种方法,可以在被试观看视频时记录她的神经模式,将其转化为计算机代码,并生成原始图像的模糊近似值。也许有一天,这个过程会被完善和逆向工程化,为初学者提供“神经可下载的”(neuro-downloadable)意大利语多媒体课程。
这个方法的潜力是显而易见的,且不仅是对像我这样过于繁忙的语言怪才而言。各个领域的学生都能以比现在快一倍的速度达到熟练程度,并学到双倍的知识。任何人想要获得新的工作技能、掌握一门乐器或探索错综复杂的粒子物理学,都能以近乎神奇的速度轻松实现。
那么,代价是什么呢?
但风险似乎也是显而易见的。睡眠教学法可能会破坏睡眠中通常会出现的恢复功能——例如,修剪多余的神经连接,为即将到来的记忆腾出空间。经过一夜无意识考试后,第二天学习新知识可能会变得更加困难。睡觉时学习也会减少大脑用于巩固长期记忆的能量,也许会导致去年伊斯坦布尔之行的记忆被抹去。它可能会破坏神经胶质细胞夜间清理大脑代谢废物的功能,增加学习者患神经退行性疾病(如阿尔茨海默病)的可能性。
睡眠期间,大脑会重新平衡免疫和内分泌系统,这就是为什么睡眠障碍与抑郁症、肥胖症、糖尿病、心血管疾病和癌症等疾病相关。摆弄大脑的控制过程可能会带来严重后果。
此外,还必须考虑到不太明显的代价。我已经上了年纪,还记得智能手机出现之前的生活,那会儿,在一天中的某些时间,甚至连续几天失联,都是完全可以接受的。这种失联的宁静状态现已成为“失落的伊甸园”。如今,若我的编辑发来紧急询问邮件,我没有理由不在清醒时回复。但至少,睡眠时间仍是禁区。但在睡眠教学法盛行的未来,这种界限也可能消失。
想象一下,你老板要求你在熄灯后,将明早要报告的数据下载到大脑中。想象一下,你的同事们在墨菲斯*的怀抱里,讨论他们追的电视剧。想象一下,你的脸书好友们会发布他们每晚学习普通话的最新情况。如果我们屈从于24小时可触达、可通信和可生产的要求,我们将牺牲什么?
*译者注:墨菲斯(Morpheus),希腊神话里的梦神。
臣服于睡眠吧,就像臣服于爱情
睡眠心理学家鲁宾·奈曼(Rubin Naiman)在其著作《治愈之夜》中讲述了他小时候与母亲玩的一个游戏。他母亲会问:“世界上最好的东西是什么?”小鲁宾会大声说出自己的猜测(“玩具!卡通!雪糕!”),直到她说出正确答案:“夜晚。”
奈曼的母亲曾在纳粹集中营度过了四年,在那段地狱般的生活中,她学会了珍惜黑暗中的时光,将其视为应许之地。“夜晚带来睡眠”,奈曼写道,“这是每日重要的安宁。相应的,睡眠又是通往梦的天然桥梁。而梦境则为我们打开了一个神秘入口,通向一个更可塑的、更具同情心的现实。”
奈曼观察到,这种敬畏在传统社会中很常见,但在被过度照明的西方,它几乎被抛弃了。我们大多数人认为,夜晚是一种不便,而睡眠只不过是为第二天充电的一种手段。我们尽可能少睡觉,当睡眠不能如期而至时,就吃药让自己昏昏欲睡。然后,我们用兴奋剂来弥补真正休息时间的不足。奈曼论证,我们“以醒来为中心”的世界观,正在损害我们的精神、身体和心理健康。他认为,我们能通过“恢复夜晚和夜间意识的神圣感”来收获益处。
当我问奈曼对睡眠教学法的看法时,他把它比作用做爱来消耗卡路里,或边上厕所边吃东西。他告诉我,睡眠是消化数据的时间,而不是摄取数据的时间。睡眠也是我们放弃昼伏夜出的追求,徜徉在内心隐秘中的时刻。奈曼说:“我们谈论坠入爱河和入睡,两者都需要一种臣服。”睡眠的主要乐趣之一(就像爱情一样),是它把我们从时间中拉出来,进入一个每刻都是奖励的领域。
相比之下,睡眠学习法则是拒绝进入无意识的睡眠状态。它代表了“唤醒中心主义”(wake-centrism)的终极目标:完全征服黑夜,把它变成一个完全可以利用的殖民地。在这样的环境中,不戴耳机上床睡觉就像出门不带手机一样不可想象。在世界的某处,一个新时代的萨利格肯定正在暗中策划从这样的场景中获利。
我特此挂上“请勿打扰”的标志。拜托了,阿洛伊斯,让我睡觉吧!
原文:https://aeon.co/essays/if-we-can-learn-while-asleep-when-will-we-ever-switch-off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神经现实 (ID:neureality),作者:Kenneth Miller,翻译:绒球兔纸,审校:一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