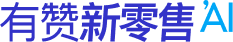当人们说起曼哈顿计划(Manhattan Project)时,大概率首先想起的是被称为“原子弹之父”的奥本海默(J. Robert Oppenheimer,1904—1967)。事实上,奥本海默并不参与原子弹爆炸原理的研究与具体的复杂计算,承担这一任务的是曼哈顿计划的理论部,这是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中最重要的部门。
理论部主任贝特(Hans Albrecht Bethe, 1906—2005)位于这个智力金字塔的顶端。在他的带领下,理论部克服种种困难,解决了原子弹研制过程中的众多重要理论问题,保证了项目的成功。
贝特。图片来源:Los Alamos National Laboratory
贝特同时是一名杰出的物理学与天体物理学大师。他被任命为曼哈顿计划理论部的主任,正因为他此前已是美国核物理领域的领军人物。他的科研生涯持续了至少70年,其中有至少50年持续处于巅峰期。在此期间,他转战不同领域,均获得重要的,甚至划时代的成果,表现出过人的天赋、勤奋与创造力。由于系统而深入研究了主序恒星(包括太阳)内部的核聚变过程,他获得1967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奖理由是,“他对核反应理论的贡献,特别是关于恒星内能量产生的发现。”
本文介绍贝特的生平与科学贡献。
学术世家的骄子
1906年7月2日,贝特诞生于当时属于德国的斯特拉斯堡(Strasbourg,现在属于法国)。
贝特的父亲阿尔布雷希特·贝特(Albrecht Julius Theodor Bethe,1872—1954)是一名生理学家,主要研究无脊椎动物的神经系统。阿尔布雷希特于1895年在慕尼黑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于1896年到1911年在斯特拉斯堡生理学研究所工作,于1898年在那里获得医学博士学位[1]。
贝特的外公亚伯拉罕·库恩(Abraham Kuhn,1838—1900)是斯特拉斯堡大学的教授,他的女儿安娜·库恩(Anna Kuhn,1876—1966)嫁给阿尔布雷希特后改名为安娜·贝特-库恩(Anna Bethe-Kuhn)。贝特出生时,他外公已经逝世。
1911年,阿尔布雷希特成为基尔大学生理学研究所的教授和主任。1915年,阿尔布雷希特成为法兰克福大学生理学研究所所长[2]。这两次任命使贝特一家两次搬家,贝特也因此辗转多个学校读书。
12岁时的贝特与父母的合照。图片来源:公共版权
1924年,贝特高中毕业,进入法兰克福大学攻读化学专业学位。事实证明,贝特不适合这个专业,因为他的实验能力很差,屡次出问题;最严重时,他把硫酸洒到了自己的实验服上。这一点,他与后来的好友奥本海默同病相怜。
1926年4月,在老师的建议下,贝特转学到慕尼黑大学,师从著名理论物理学家索末菲(Arnold Sommerfeld,1868—1951)。擅长理论研究的贝特从此如鱼得水。索末菲建议贝特以晶体中的电子衍射作为研究课题,他也由此进入固体物理学领域。
1928年,22岁的贝特获得博士学位,次年入职斯图加特工业大学。
年轻有为
1929年,贝特发表了数篇论文,研究包括氢原子电子能的对称、氦气体的电子分布、晶体分离等课题,这些课题涉及量子力学与固体物理学。在索末菲的推荐下,贝特获得洛克菲勒基金会(Rockefeller Foundation)提供的游学奖学金(Travelling Scholarship),每个月150美元(相当于2023年的约2765美元)。
1930年,贝特发表了长达76页的论文《高速粒子射线通过物质的理论》[3]。这篇论文从薛定谔方程出发,利用傅里叶变换,获得著名的“贝特公式”(Bethe formula)。这个公式描述粒子通过介质时的平均能量损失。贝特后来认为这是自己一生中最伟大的论文(没有“之一”),当时他才24岁。这篇论文至今为止被引用了6千多次。
同年,贝特利用游学奖学金访问剑桥大学卡文迪什实验室,做福勒(Ralph Fowler,1889—1944)的博士后。布莱克特(Patrick Blackett,1897—1974)希望他能够将“贝特公式”推广到相对论情形,以描述极端高速的粒子。贝特满足了布莱克特的愿望,将推广后的公式写入论文《相对论性电子减速公式》[4],于1932年发表。
在剑桥大学期间,贝特还与同一实验室的年轻人合作编造了一篇写给编辑部的恶作剧“论文”[5]。这篇“论文”以摄氏度为单位计算绝对零度时的精细结构常数,以嘲笑当时一些物理学家拼凑物理学常数。天体物理学大师爱丁顿(Arthur Eddington,1882—1944)就曾经用一些数字拼凑精细结构常数的值。(编者注:参见《他是天体物理学的一代宗师,也是学科发展的绊脚石?》)贝特等人在此后道歉。[6]
按照计划,贝特用剩下的一半奖学金访问罗马大学费米(Enrico Fermi,1901—1954)的物理实验室。费米的过人才智折服了贝特,令他感到相见恨晚。另一方面,贝特也被认为是访问费米实验室的人中最杰出的一位。贝特从索末菲那里继承了严谨的风格,从费米那里继承了简洁的风格。
“贝特假设”
1931年3月,贝特发表了早期的代表作《关于金属的理论. I. 线性原子链的本征值与本征函数》[7]。这篇论文提出了著名的“贝特假设”(Bethe ansatz),用以精确计算一维量子多体模型问题,寻找某些量子多体模型的波函数的精确本征值与本征函数。至今为止,这篇论文获得4700多次引用。物理学大师费曼(Richard Feynman,1918—1988)在逝世前写在黑板上的待学习(To learn)主题之一就是“贝特假设问题”(Bethe ansatz problems)。而当年贝特发表这篇论文时,还未满25岁。
在罗马访学期间,贝特还与费米合作,研究量子电动力学(QED)。QED是描述电子/正电子(物质)与光子(辐射)相互作用的一门物理学分支。贝特与费米合作了一篇QED领域的论文《两个电子的相互作用》[8],它于1932年发表。
贝特1932年还写了两篇综述。第一篇的主题是氢和氦的量子力学,第二篇的主题是金属中的电子。1959年,巴彻(Robert Bacher,1905—2004)与韦斯科普夫(Victor Weisskopf,1908—2002)为了再次出版贝特那篇关于量子力学的综述而认真阅读,发现它博大精深,仅需要极少的更新即可再版。
贝特-海特勒公式
结束游学后,贝特回到德国,并于1932年成为图宾根大学的助理教授。然而,纳粹德国很快开始排犹。由于贝特的母亲有1/2犹太血统,他也受到牵连而被大学解雇。在英国物理学家小布拉格(William Lawrence Bragg,1890—1971)的帮助下,贝特于1933年获得曼彻斯特大学提供的聘期一年的讲师职位,迅速前往英国。
在英国期间,贝特与同为德国人的佩尔斯(Rudolf Peierls,1907—1995)成为好友,他也因为犹太血统而逃离德国。在其影响下,贝特开始研究核物理。后来佩尔斯成为英国的原子弹计划(“合金管计划”)的负责人,并在二战晚期与贝特再次相遇,在原子弹制造方面进行合作。
由于出色的学术能力,贝特很快先后获得布里斯托尔大学与康奈尔大学的聘用。康奈尔大学允许贝特履行完布里斯托尔大学的合同后再入职。
1934年,贝特与海特勒(Walter Heinrich Heitler,1904—1981)合作发表了论文《关于快粒子的停止和正电子的产生》[9],研究了原子与分子对光子的散射以及光子湮灭为电子与正电子对的过程。这篇论文提出了著名的“贝特-海特勒公式”。这篇经典文章被引用超过2500次。
“贝特圣经”
1935年2月,贝特入职康奈尔大学。在这里他研究做得风生水起,并与泰勒(Edward Teller,1908—2003)等人成为好友。
1936年—1937年,贝特连续发表三篇核物理领域的重磅论文,第一篇论文与巴彻(第二作者)合作,讨论原子核的稳定性[10];第二篇为贝特独自撰写,讨论原子核动力学的理论[11];第三篇论文与利文斯顿(Milton Livingston,1905-1986,第一作者)合作,讨论原子核动力学的实验[12]。
这三篇论文在核物理领域拥有崇高地位,被当时的一些学者称为“贝特圣经”(Bethe’s Bible)。
意气风发的贝特写信给母亲,说:“我是美国名列前茅的理论家。这并不意味着我是最好的。维格纳(Eugene Wigner,1902—1995)当然更好,奥本海默和泰勒可能与他一样好。但我做得多,说得多,这也很重要。”[6]
1937年,贝特在杜克大学讲学时遇到罗斯·埃瓦尔德(Rose Ewald,1917—2019),她也因为纳粹德国的迫害而逃到美国。罗斯的父亲保罗·埃瓦尔德(Paul Ewald,1888—1985)是著名的晶体学家与物理学家、X射线衍射法的先驱;他的博士导师也是索末菲,因此他是贝特的同门师兄。因为这层关系,罗斯在十几岁时就在德国见过贝特。在杜克大学遇见后,二人成为恋人,并在1939年9月结婚。
贝特妻子埃瓦尔德(1967年)。图片来源:公共版权
盗火的普罗米修斯:破解恒星能源之谜
早在1920年,爱丁顿就在论文中指出,恒星大部分时期的能源不是来自恒星的收缩,而是来自氢原子核(质子)的聚变。但是,爱丁顿没有给出氢聚变为氦的具体过程。
1937年,伽莫夫(George Gamow,1904—1968)和魏扎克(Carl von Weizsäcker,1912—2007)提出,太阳核心的质子与质子通过“质子-质子链”(pp链)反应聚变为氦,释放出能量。此外,魏扎克在1937年与1938年还提出碳氮氧(CNO)循环过程。不过,这些工作尚未给出一些重要的具体过程。
pp链的基础是质子聚变为氘(D)的反应,即pp反应:两个质子聚变为氘,同时释放出一个正电子与中微子。魏扎克建议贝特研究pp反应。几乎同时,伽莫夫也让学生克里奇菲尔德(Charles Critchfield,1910—1994)计算pp反应。后者在1938年初完成这个计算,伽莫夫建议将此文发给贝特审阅,因为贝特在双核子反应方面做过很多计算[13]。贝特确认克里奇菲尔德计算正确。二人因此合作了论文《质子组合形成氘》。[14]
贝特与克里奇菲尔德计算的过程如下:两个质子结合为氘、氘与质子结合为氦-3,氦-3与氦-4结合铍-7,铍-7衰变为锂-7,锂-7与质子结合为2个氦-4。
后来的研究表明,pp链有4种类型。贝特与克里奇菲尔德当时计算的是现在所说的II型pp链。太阳核心温度为1570万K,其核心的氢聚变以I型pp链为主要模式,它为太阳贡献了81.6%的能量;II型pp链为太阳贡献了16%的能量。尽管他们没有考虑其他类型的pp链,但他们对II型pp链的计算已足够重要与卓越。
让二人感到困扰的是,如果太阳核心温度是爱丁顿此前估计的4000万K,将这个值代入计算后,得到的亮度远超过观测到的太阳亮度。
1938年3月17日,贝特应邀参加了伽莫夫与泰勒举办的第四届华盛顿理论物理年会。这次年会的主题是“恒星能量的产生”。贝特本来不想接受这个邀请,因为他当时的兴趣依然在QED。但是,在泰勒的劝说下,他还是参会了。[13]
这次会议上,斯特罗姆格伦(Bengt Strömgren,1908—1987)宣布,根据他对太阳化学成分的分析与计算,太阳核心的温度约为1500万K,而不是4000万K。将1500万K代入贝特与克里奇菲尔德的计算后,得到的太阳亮度与观测亮度很吻合。这对贝特等人是一个鼓舞。
会议结束后,贝特思考质量更大的恒星内部的核反应。恒星质量越大,核心温度越高,内部产能率也越高。贝特知道,比氦-4更重的元素中,锂、铍、硼都太稀有,因此他认为碳是可能的反应起点。[13]
经过2个星期的思考与计算[13],贝特重新发现了CNO循环反应。贝特发现的循环过程为:碳-12→氮-13→碳-13→氮-14→氧-15→氮-15→碳-12。在整个过程中,碳、氮、氧起到催化剂作用,自身不被消耗。
I型CNO循环过程。图中H、He、C、N、O、ν与γ分别为为氢、氦、碳、氮、氧、中微子与伽玛光子。图片来源:Borb
此后,实验物理学家用高速质子轰击碳-12靶,很快发现了氮-13衰变的证据。这证明贝特的计算是正确的。后来的研究表明,恒星内部的氢通过CNO循环过程聚变为氦的渠道有多个。魏扎克与贝特发现的都是I型CNO循环过程,它也因此被称为“贝特-魏扎克循环”(Bethe-Weizsäcker cycle)。
贝特将研究成果写入论文《恒星能量的产生》[15]。在这篇论文中,贝特还进一步仔细计算了pp链的反应率,并指出:类似于太阳等质量较小的恒星,内部能量主要来自pp链反应;大质量恒星的内部能量主要来自CNO循环。这个结论至今依然正确。
贝特的论文给出的两种产能方式的产能率与温度(单位为100万K)的关系。点虚线为pp链,虚线为CNO循环,实线表示两者之和。当恒星核心温度低于1500万K时,pp链贡献了绝大部分能量;反之,CNO循环贡献了绝大部分能量。图片来源:参考文献[15]
贝特将《恒星能量的产生》投到《物理学评论》(Physical Review)。不久后,贝特的博士研究生马沙克(Robert Marshak,1916—1992)注意到,纽约科学院正在悬赏500美元(相当于2023年的10915美元),征求太阳和恒星能源的最佳论文,条件是论文尚未发表。[13]
马沙克立即把消息告诉贝特。贝特赶紧撤回论文,把它寄到纽约科学院,赢得500美元奖金。他分给马沙克50美元,作为信息费。然后,他给德国政府寄了250美元,以确保当时正准备逃离德国的母亲搬家时,所有要搬走的物品可以得到妥善处理。[13]
最后,这篇划时代的论文被贝特重新投给《物理学评论》,并于1939年3月被发表。这篇论文的结果不仅适用于太阳,而且适用于所有处于主序阶段的恒星(处于核心氢聚变状态的恒星)。恒星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处于主序阶段。
曼哈顿计划的灵魂人物
二战在欧洲爆发后,大量学者开始投身于武器设计有关的课题。贝特也不例外,他与泰勒合作研究弹头穿过气体时的冲击波理论。他还研究了装甲穿透理论,不过该理论立即被军队列入机密,尚未成为美国公民的贝特因此无法进一步涉足。
1941年3月,贝特获得美国国籍,这为他从事军事科研扫除了最大障碍。1941年12月,贝特终于获得安全许可,加入麻省理工学院的辐射实验室。在那里,他发明了可用于雷达组的“贝特孔定向耦合器”(Bethe-hole directional coupler)。
曼哈顿计划正式启动后,奥本海默被任命为科学主任,统筹所有部门。这些部门中,理论部负责进行理论计算,确定各种方案的可行性,因此是最关键的部门。奥本海默想自己兼任理论部主任。
然而,在奥本海默征询好友拉比(Isidor Rabi,1898—1988)对曼哈顿计划的意见时,拉比给了两个建议:不要穿军队制服;请贝特当理论部主任。奥本海默虽然桀骜不驯,但却对拉比毕恭毕敬,言听计从;何况他也知道当时的贝特虽然还很年轻(35岁),但已经是核物理学领域的泰斗。贝特因此被邀请担任理论部主任。
曼哈顿计划期间的贝特身份证照片,其ID编号为K3。图片来源:Los Alamos National Laboratory
上任之后,贝特带领理论部的成员计算了铀235的临界质量(使链式反应可以进行的最小质量)、效率、裂变增殖、爆炸的流体动力学、中子引发剂、爆炸的辐射传播等关键问题。他还与理论组成员费曼一起开发了计算原子弹爆炸当量的公式。[16]
在紧张的研发关键时刻,贝特起到了稳定军心的作用:泰勒通过计算表明核爆炸会导致地球大气中的氮聚变为镁并释放出氦离子,释放巨大能量从而将大气烧毁;贝特第一时间就认定这个计算是错误的。接着他通过严格的计算证明了自己的判断,并指出泰勒的计算基于一个错误的假设。贝特的计算为奥本海默提供了足够的信心。(这也是诺兰电影《奥本海默》中的桥段。)
由于曼哈顿计划的工作,贝特在纯科学领域的研究一度大幅度减少。1944年,他似乎腾出了更多时间,发表了一篇研究电磁波圆孔衍射的论文[17],对古老的衍射问题进行了新的深入研究。这篇文章至今为止被引用3700多次。
1945年7月16日,曼哈顿计划的参与者们执行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核试验——“三位一体”(Trinity)试验,世界上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贝特带领的理论组为其成功提供了至关重要的贡献。爆炸后测出的各种数据验证了理论部计算结果的准确性。
在曼哈顿计划的执行过程中,理论部是所有部门中花费最少、声望最高的部门。作为理论部主任,贝特的作用不亚于统筹全局的奥本海默。事实也证明了拉比的眼光:贝特不仅拥有杰出的物理学才能,也有卓越的团队领导能力。可以说,贝特是曼哈顿计划的灵魂人物。
火车上的计算:量子电动力学
二战结束后,原本服务于战时军工科技的科学家纷纷回到大学或研究所。贝特回到康奈尔大学,继续做科研。此时的奥本海默已不做研究,贝特成为当时全美理论物理学的领袖。贝特还把自己在参与曼哈顿计划期间结识的一些杰出的年轻人(如费曼)延揽到康奈尔大学,这里成为当时世界上理论物理的顶尖研究中心之一。
此时整个理论物理学的核心是QED。1947年,兰姆(Willis Lamb,1913—2008)与雷瑟福(Robert Retherford,1912—1981)在实验室精准测出了氢原子的2S1/2和2P1/2这两个能级的能量差对应的频率为1057 MHz,即“兰姆移位”(Lamb shift)。然而,根据此前的理论,这两个能量应该是相等的。这意味着此前的理论必须被修正。
1947年6月,著名的谢尔特岛会议在纽约谢尔特(Shelter)岛的一家宾馆召开,主题为“量子力学基础”(Foundations of Quantum Mechanics)。这次会议讨论的热点之一是兰姆移位的产生机制。荷兰物理学家克莱默斯(Hans Kramers,1894—1952)提出“重新正规化”(重正化,renormalization)方案,但他无法进行定量计算。
谢尔特岛会议重新激起贝特对QED的兴趣。贝特认为出现兰姆移位的原因是:电子释放出虚光子后,又将虚光子吸收回去,这个过程产生了电子的“自能”。会议结束后,贝特坐火车前往位于纽约州东部的斯克内克塔迪(Schenectady)。
在火车上,贝特开始计算,他采用非相对论近似(即假设电子低速运动,不考虑相对论效应),旅途还未结束,他便完成了计算。他算出的能级差异是1040 MHz,与实验测出的1057 MHz非常接近。
贝特很快写好相关论文,并于1947年8月将其发表于《物理学评论》。这篇标题为《电磁能级移位》[18]的论文只有3页,只包含12个数学方程,但它影响深远:它给出了处理无穷大并得到有限值的一个先例,为新的QED理论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戴森(Freeman Dyson,1923—2020)也是在这个时期来到康奈尔大学跟随贝特读研究生。贝特让戴森重复他在电子方面的计算,并给出一个低阶修正。戴森经过几个月的复杂计算,发现得到的结果和此前贝特得到的结果没有本质差异。不过,这几个月的训练让本来没有物理学背景的戴森熟悉了QED。此后,戴森在QED领域大显身手,折服了奥本海默,并因此于1952年被后者聘为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研究员。[19]
氢弹的“助产士”
原子弹成功爆炸后,早在曼哈顿计划期间就吵着要制造氢弹的泰勒要求继续研究氢弹。由于奥本海默等人的强烈反对,项目一直无法上马。1949年8月29日,苏联成功引爆了原子弹,核军备竞赛正式开启。1950年1月底,时任美国总统杜鲁门拍板,启动氢弹的研制。
核军备竞赛的启动与冷战的升级让一开始反对研制氢弹的贝特担忧双方力量失衡,因此转而投入氢弹的研制之中。
1951年5月9日,泰勒团队研制的世界上第一颗氢弹被成功引爆,其威力相当于广岛原子弹的10倍。1952年11月1日,第二颗氢弹被引爆,其威力相当于广岛原子弹的450倍。
很多人称泰勒为氢弹之父,另外一些人认为乌拉姆(Stanisław Ulam,1909—1984)才是氢弹之父。贝特认为,乌拉姆为氢弹之父,泰勒是氢弹之母,而他自己是助产士。
贝特说自己对氢弹项目的贡献微不足道:“我做得非常少。我认为我的主要贡献是:我在一次会议上说1英寸是2.54厘米,而不是2.5厘米。(此前)工程师们被2.5束缚住了,所以厘米尺寸和英寸尺寸始终不一致。所以,我解决了这个问题。”[20]
这个说法显然是自谦,同时是借机调侃日常使用的英寸制被用于科学技术研究。事实上,据戴森回忆[19],贝特有大约8个月时间没出现在康奈尔大学,行程保密。而氢弹成功爆炸后,贝特重回校园。显然这8个月,贝特在项目组内进行大量计算工作。
氢弹爆炸后,泰勒意图继续制造更多更强的氢弹,与苏联进行核竞赛。贝特的意见相反,他希望美苏两国可以谈判,实现核裁军,避免人类被核大战毁灭。在奥本海默被进行安全审查时,贝特劝泰勒不要出席指控奥本海默(他的劝说没有成功)。同时,贝特坚定维护奥本海默,并在听证会上一度代表他。贝特说,虽然奥本海默反对研制氢弹,但他的立场并未阻碍氢弹研制的进度。
故地重游:核物理与粒子物理学
从50年代到70年代,贝特将更多精力投入到核物理与粒子物理学的研究之中,对原子核、电子、介子、粒子对、韧致辐射等众多课题进行深入研究。
1951年,贝特与萨尔皮德(Edwin Salpeter,1924—2008)合作发表论文《束缚态问题的相对论性方程》[21]。这篇论文研究了由两个粒子构成的束缚态系统,提出了著名的“贝特-萨尔皮德方程”(Bethe-Salpeter equation),其解为“贝特-萨尔皮德振幅”(Bethe-Salpeter amplitude)。
束缚态系统在粒子物理学中普遍存在,如:由夸克与反夸克构成各种介子,由电子与正电子构成的束缚态,由电子与空穴构成的束缚态等。贝特与萨尔皮德给出了研究这些束缚系统的相对论性量子场论方法,对于此后物理学家研究此类系统有重要意义。
1954年-1968年,贝特第一作者或以唯一作者发表的重要论文包括《韧致[辐射]与[粒子]对生产理论. I. 微分截面》[22]、《核多体问题》[23]、《核物质的参考谱方法》[24]、《核物质的三体相关性》[25]、《核子的托马斯-费米理论》[26]。这些论文至今均有数百次引用,其他论文更不胜枚举。贝特的勤奋、高产与论文的高品质是惊人的。
超新星研究
1975年,69岁的贝特从康奈尔大学退休。1978年开始,贝特与布朗(Gerry Brown,1926—2013)合作研究“核塌缩型超新星”的机制,此类超新星由大质量恒星塌缩后爆炸而形成。
在贝特进入超新星领域之前,这个领域的学者认为恒星塌缩后,核心密度被压缩到原子核密度的0.1倍时,塌缩就会停止。贝特很快证明:恒星内核被压缩到密度超过原子核密度后,塌缩才会停止。[13]
贝特与其他学者的研究还表明,核塌缩型超新星爆发后不久,内部产生的反弹激波就会被耗尽能量。1980年,贝特研究了中子星发出中微子的性质。1982年,威尔逊(James Wilson,1922—2007)提出“中微子延迟爆发”机制:核心释放出的大量中微子与稠密的外层物质相互作用,将其中的一小部分能量传递给物质,将恒星炸开。此后,贝特与威尔逊深入研究了这个机制,他们于1985年发表的一篇论文[27]成为这个课题的经典之作。
1987年1月,贝特与布朗决定放弃超新星爆炸机制的研究,因为这方面的研究一直没有观测方面的证据。然而,就在一个月后,人类观测到大麦哲伦云(LMC)内一颗超新星爆发,即SN 1987A。LMC距离地球约17万光年,SN 1987A爆发后,它发出的光在太空中穿行了约17万年,才到达地球。
超新星SN 1987A爆发后(左)与爆发前(右)的图像。图片来源:见图下方
这是一颗核塌缩型超新星,它发出的中微子被地球上的两个中微子探测器探测到,这直接支持了中微子延迟爆发理论。这颗超新星重新激发起贝特对超新星爆炸机制的研究热情,他在此后研究了超新星爆炸时的对流与快速核合成过程。
1990年,84岁的贝特写了一篇长篇综述[28],总结核塌缩型超新星爆发的研究。这篇综述在很长一段时间都是这方面的权威综述。年迈的贝特仍笔耕不辍,他与布朗在超新星方面的合作一直持续到1995年。
在研究超新星爆发机制的过程中,贝特经常使用1051尔格(等于1044焦耳)作为能量单位。后来研究超新星的学者经常将这个量称为“1贝特”,简称1 B。这个量也被缩写为“foe”。
双星并合与引力波
1996年,在贝特与布朗访问加州理工学院时,索恩(Kip Thorne,1940—)寻求他们的帮助。当时索恩正在为制造激光干涉引力波天文台(Laser Interferometer Gravitational-Wave Observatory,LIGO)而奋斗。LIGO可以探测的引力波主要来自双黑洞并合、双中子星并合、黑洞-中子星合并等过程。
索恩希望贝特与布朗计算LIGO每年可探测到多少黑洞-中子星并合产生的引力波事件。二人计算了中子星-黑洞并合与双中子星并合事件的发生率[29],并指出:LIGO每个月可以发现几例由双致密星并合导致的引力波,而不是此前别人估计的每年两三例。[13]
贝特、布朗以及贝特的助手还研究了中子星-白矮星并合等新类型。此外,他还与合作者研究了涉及X射线与伽玛射线暴的黑洞系统以及具有共同包层的双星系统(双星过于接近,导致双星的外层物质包裹着双星,如同花生壳裹着花生)等课题。
2015年开始,升级后的LIGO先后探测到双黑洞并合与双中子星并合产生的引力波,并很可能探测到黑洞与中子星并合发出的引力波。
20世纪最强解题大师
由于贝特在pp链与CNO循环的深入研究有力推动了人类对恒星能源的理解,他从1943年开始就被提名为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并在1967年获奖。从1943到1967年这25年时间内,他有19年被提名。在他获奖的消息传开后的几个月内,他家的电话成为热线电话,甚至有同姓的陌生人写信给他,说是他的亲戚,请求分享诺贝尔奖的部分奖金。[13]
除诺贝尔物理学奖之外,贝特还先后获得亨利·德雷珀奖章(Henry Draper Medal,1947;编者注:关于德雷珀可参见《他是一名医生,却改变了天文学》)、普朗克奖章(Max Planck Medal,1955)、富兰克林奖章(Franklin Medal,1959)、爱丁顿奖章(Eddington Medal,1961)、费米奖(Enrico Fermi Award,1961)、拉姆福德奖(Rumford Prize,1963)、美国国家科学奖章(National Medal of Science,1975),奥兹特德奖章(Oersted Medal,1993),布鲁斯奖章(Bruce Medal,2001)等重要奖项。看来负责颁发爱丁顿奖章的英国皇家天文学会并未介意他当年的那篇恶作剧文章对爱丁顿等人的影射。
为了表示对贝特的尊崇以及奖励那些在天体物理学、核物理与核天体物理等领域做出杰出成就的学者,美国物理学会设立了贝特奖。贝特奖从1998年开始颁发。
2003年,97岁高龄的贝特应《天文与天体物理学年鉴》(Annual Review of Astronomy & Astrophysics)的邀请,在儿子亨利·贝特(Henry George Bethe,1944—2015)的协助下,撰写并发表了《我的天体物理学生涯》(My Life in Astrophysics)[13],总结了自己在天体物理学上的探索历程。
《我的天体物理学生涯》上的贝特照片与下方的签名。图片来源:Bethe, H. A. My Life in Astrophysics, 2003, ARA&A, 41, 1
2005年3月6日,贝特逝世,享年98岁(未到99岁生日)。他的妻子于2019年12月24日逝世,享年102岁。
2012年,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施韦伯(Silvan S. Schweber)撰写的贝特传记《核力:物理学家汉斯·贝特的成就》(Nuclear Forces: The Making of the Physicist Hans Bethe)。[6]此书主标题“Nuclear Forces”是一个巧妙的双关语,既指原子核之间的“核力”(使原子核不解散的力),也指核武器的力量。这个双关语指向了贝特的两个重要身份:核物理学研究领域的泰斗,原子弹制造过程中的主角之一。
贝特传记Nuclear Forces The Making of the Physicist Hans Bethe的封面。图片来源: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贝特的贡献当然远远不限于原子弹与核物理。在他持续70多年的科学生涯中,他对量子力学、固体物理学、核物理、天体物理学、量子电动力学与粒子物理学等多个领域都做出杰出贡献,而且每10年就有至少一个重要成果;在巅峰阶段,其重要成果更密集。
长期处于巅峰状态且成就斐然的科学家寥寥无几,贝特是其中之一。戴森说他是“20世纪最强问题解决者”(supreme problem-solver of the 20th century)[30],绝非过誉。
参考文献
[1] Bethe, Albrecht. The Virtual Laboratory (https://vlp.mpiwg-berlin.mpg.de/people/data?id=per362)
[2] Stahnisch, FW (2016). “From ‘Nerve Fiber Regeneration’ to ‘Functional Changes’ in the Human Brain-On the Paradigm-Shifting Work of the Experimental Physiologist Albrecht Bethe (1872-1954) in Frankfurt am Main”. Front Syst Neurosci. 10: 6. (https://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4766753/)
[3]Bethe, H. Zur Theorie des Durchgangs schneller Korpuskularstrahlen durch Materie, 1930, AnP, 397, 325
[4] Bethe, H. A. Bremsformel für Elektronen relativistischer Geschwindigkeit, 1932, ZPhy, 76, 293
[5]Corlin, A., Stein, J. S., Beck, G., & Bethe, H. & Riezler, W. Zuschriften, 1931, NW, 19, 37
[6]Schweber, Silvan S. (2012). Nuclear Forces: The Making of the Physicist Hans Bethe.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ISBN 978-0-674-06587-1.
[7] Bethe, H. A. Zur Theorie der Metalle. I. Eigenwerte und Eigenfunktionen der linearen Atomkette, ZPhy. 71 (3–4): 205
[8]Bethe, H. A. & Fermi, E. Über die Wechselwirkung von zwei Elektronen, 1932, ZPhy, 77, 296
[9]Bethe, H. & Heitler, W. On the Stopping of Fast Particles and on the Creation of Positive Electrons, 1934, RSPSA, 146, 83
[10] Bethe, H. A. & Bacher, R. F. Nuclear Radius and Many-Body Problem, 1936, PhRv, 50, 977
[11] Bethe, H. A. Nuclear Physics B. Nuclear Dynamics, Theoretical, 1937, RvMP, 9, 69
[12] Livingston, M. S.; Bethe, H. A. Nuclear Physics C. Nuclear Dynamics, Experimental, 1937, RvMP, 9, 245
[13] Bethe, H. A. My Life in Astrophysics, 2003, ARA&A, 41, 1
[14] Bethe, H. A. & Critchfield, C. L. The Formation of Deuterons by Proton Combination, 1938, PhRv, 54, 248
[15] Bethe, H. A. Energy Production in Stars, 1939, PhRv, 55, 434
[16]Hoddeson, Lillian; Henriksen, Paul W.; Meade, Roger A.; Westfall, Catherine L. (1993). Critical Assembly: A Technical History of Los Alamos During the Oppenheimer Years, 1943–1945.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ISBN 0-521-44132-3. OCLC 26764320.
[17]Bethe, H. A. Theory of Diffraction by Small Holes, 1944, PhRv, 66, 163
[18] Bethe, H. A. The Electromagnetic Shift of Energy Levels, 1947, PhRv, 72, 339
[19] Freeman Dyson, Disturbing the Universe. Harper & Row. 1979. ISBN 978-0-06-011108-3.
[20]Manhattan Project Spotlight: Hans and Rose Bethe (https://ahf.nuclearmuseum.org/manhattan-project-spotlight-hans-and-rose-bethe/)
[21] Salpeter, E. E. & Bethe, H. A., A Relativistic Equation for Bound-State Problems, 1951, PhRv, 84, 1232
[22]Bethe, H. A., & Maximon, L. C. Theory of Bremsstrahlung and Pair Production. I. Differential Cross Section, 1954, PhRv, 93, 768
[23]Bethe, H. A. Nuclear Many-Body Problem, 1956, PhRv, 103, 1353
[24]Bethe, H. A., Brandow, B. H., & Petschek, A. G. Reference Spectrum Method for Nuclear Matter, 1963, PhRv, 129, 225
[25]Bethe, H. A. Three-Body Correlations in Nuclear Matter, 1965, PhRv, 138, 804
[26]Bethe, H. A. Thomas-Fermi Theory of Nuclei, 1968, PhRv, 167, 879
[27]Bethe, H. A. & Wilson, J. R. Revival of a stalled supernova shock by neutrino heating, 1985, ApJ, 295, 14
[28]Bethe, H. A. Supernova mechanisms, 1990, RvMP, 62, 801
[29] Bethe, H. A. & Brown, G. E. Evolution of Binary Compact Objects That Merge, 1998, ApJ, 506, 780
[30]Wark, David, The Supreme Problem Solver, Nature, 445, 7124, 149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返朴 (ID:fanpu2019),作者:王善钦,科普中国出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