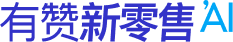说起“聪明动物”,我们会想起谁?是“边牧是边牧,狗是狗”的边境牧羊犬,“人类的表亲”大猩猩,还是“在捕猎时懂得团队合作、拯救过遇袭潜水员”的虎鲸?
生活在澳洲的人类可能有一个不同的答案:葵花凤头鹦鹉(sulfur-crested cockatoo)。
▷ 葵花凤头鹦鹉熟练地打开垃圾箱。图源:livescience
这种著名的观赏鸟类拥有漂亮的白色羽毛和绽开时如葵花的黄色冠羽。因其人工繁殖的成功和出色的学习能力,时常能在国内的动物园里看到它们的身影。然而,在葵花凤头鹦鹉的快乐老家澳大利亚,成群结队的鹦鹉们令当地居民不堪其扰——它们学会了打开各个街区不同样式的生活垃圾箱觅食,并且通过社会学习将其中的技巧在族群内广而告之。
一项发表在《科学》(Science)杂志上的论文显示,葵花凤头鹦鹉的“开箱偷食”行为传播迅速,由2018年前的三个悉尼郊区迅速扩增到2019年的44个。研究人员甚至观察到了由森林阻隔而形成的地域特征,每个片区里葵花凤头鹦鹉的开箱方法都有一些细微的不同[1]。这些聪明的鸟儿已经成功倒逼它们的人类邻居想出各种科技手段保护自家的垃圾箱,不可谓不是人与自然相处中的一项奇观。
你可能已经注意到,提起“聪明”的时候,许多人并不会第一时间想起鸟类。相比之下,与人类亲缘关系更近的哺乳动物们往往更吸引我们注意。但仔细回想,从“鹦鹉学舌”到“乌鸦喝水”,鸟类的“小聪明”的确充斥于我们的文化生活之中。行为学数据也显示,鸦类和鹦鹉在许多领域的认知能力与非人灵长类旗鼓相当[2][3]。它们不仅拥有空间记忆和情节记忆,也可以理解因果关系、延迟满足并计划未来,它们甚至拥有心智理论(一种理解自己和他人心理状态的能力)。
那么,这些小小生灵为什么这么聪明呢?
▷ 原始论文:Güntürkün, Onur, Roland Pusch, and Jonas Rose. “Why birds are smart.” Trends in Cognitive Sciences (2023). https://doi.org/10.1016/j.tics.2023.11.002
一、“大小”不重要,“内容”是关键
要想理解智慧,首先研究大脑。鸟类的聪明向一个由来已久的刻板印象发起了挑战:大脑越大越聪明。尽管科学家们无法单凭大脑的重量推测某个物种或者个体的智力水平,但在同一个分类单元里,更大更重的大脑确实能够提供更多神经元和计算能力,也因此使得其拥有者比其他“表亲”更聪明[4]。这一点在非人灵长类、鲸豚类和鸟类中都有体现。但在亲缘关系较远的跨物种横向比较中,大脑的绝对重量和相对大小就没那么重要了:鸦类和鹦鹉类仅凭借5克~20克的大脑便能与拥有400克大脑的大猩猩一较高下。
那么,这些核桃大小的脑子是怎么做到的?
2016年,一项发表在PNAS的研究指出,鸟类的大脑虽小,神经元的密度却非常高[5]。每单位体积的大脑内,鸟类大脑所包含的神经元数量能达到灵长类的两倍、小鼠的四倍。研究者提出,如此高密度的神经元含量使得鸟类的前脑(forebrain)拥有与灵长类动物相当的神经元数量。神经元是大脑进行信息处理和计算的基本单位。尽管无法单独决定大脑的计算能力上限,数量相当的神经元为鸟类发展出与灵长类动物相似的信息处理能力提供了基础。
此外,鸟类的大脑皮质神经元(pallial neurons)占比远高于灵长类动物:秃鼻乌鸦与狨猴的大脑重量相仿,但前者的大脑皮质神经元数量是后者的三倍。大脑皮质神经元能够协调不同认知过程以达成一个共同目标,因此与灵活的认知能力尤为相关。拥有大量大脑皮质神经元的秃鼻乌鸦也就比狨猴更加聪明。
另一种与灵活的认知调控相关的神经元是联络神经元(associative neurons)。联络神经元存在于感知系统和运动系统之间,与联想学习和运动学习紧密相关。与鸡、鸽子和鸵鸟相比,新喀鸦(New Caledonian crow)拥有大量的联络神经元,其数量几乎可以媲美大猩猩前额皮质(prefrontal cortex)中的联络神经元[6]。新喀鸦也确实展现出了更高的智力——它们会用叶柄制作工具,钩取狭窄缝隙中的天牛幼虫吃。
因此,高神经元密度、大量大脑皮质神经元和联络神经元为小尺寸的鸟类大脑提供了惊人的计算能力,为鸟类的聪明才智提供了一定的生理基础。
二、“充分不必要”的新皮质
鸟类和哺乳类动物自数亿年前开始分别进化,最终形成了大相径庭的前脑结构。在哺乳动物中,背侧皮质(dorsal pallium)发育成大脑皮层,其中大部分是同皮质的(isocortical)。“同皮质”是指这部分大脑皮层的各个部分长得都差不多。“同皮质”更为人熟知的名称是“新皮质”,因为这部分大脑皮层为哺乳动物所特有,在进化上更新、更近。
不光如此,哺乳动物的新皮质包含了所有有关感知、运动和联络的区域,可谓一个大包大揽的大脑结构,对认知和学习能力极为重要。也正因如此,很长一段时间内新皮质也被认为是哺乳动物智力的来源。然而,聪明的鸟儿们再次挑战了这一观点。
在鸟类中,与哺乳动物同源的背侧大脑皮层进化成了超大脑皮层(hyperpallium)。与哺乳动物的新皮质不同,鸟类的超大脑皮层仅包含了感知区域,功能上无法相提并论。大部分剩余的鸟类皮质核(pallial nuclei)则位于侧脑室下方,统称为背侧脑室嵴(dorsal ventricular ridge)。背侧脑室嵴在哺乳动物中没有同源结构,但它却在功能上补充了超大脑皮层,可以处理感知信息,也包含了运动和联络区域。
近年的研究表明,背侧脑室嵴在处理感知信息的部分呈现与哺乳动物的大脑皮层相似的分层结构和信息处理路线[7],而运动和联络区域依然是核状排列的(a nuclear arrangement)。
▷ A)鸟类大脑的分区;B)鸟类大脑的结构名称(黄字)以及与其同源的哺乳动物大脑结构(白字);C)不同的信息处理路径,C1为同皮质,C2为背侧脑室嵴,C3为超大脑皮层。图源:原始论文
这些数据表明,鸟类的大脑可能由于趋同进化,部分呈现出了与哺乳动物的大脑相似的结构和信息处理方法。至少在处理感知信息方面,这些类似同皮质的结构或许有着难以替代的绝佳优势。但鉴于背侧脑室嵴和新皮质在进化角度并不同源,且背侧脑室嵴没有完全采用新皮质的处理方式,新皮质对于聪明的大脑来说,可能只是一个“充分不必要”条件。
三、多巴胺能驱动的鸟类“前额皮质”
我们已经从神经元的数量、种类和大脑结构方面讨论了鸟类聪明的原因,发现它们与哺乳动物既有相似也有不同。接下来,我们将从大脑功能上继续探讨鸟类为什么这么聪明。
背侧脑室嵴呈核状排列的结构中,尾外侧巢状皮质(nidopallium caudolaterale)尤为重要。尾外侧巢状皮质位于背侧脑室嵴的最尾端,在功能上与哺乳动物的前额皮质极为相似,几乎参与了所有的认知过程。
更重要的是,这两处区域都拥有大脑中密度最高的多巴胺能神经元(dopaminergic neurons),并与大脑内所有联络区域和前运动结构(premotor structures)相连。与前额皮质中的多巴胺能神经元相仿,尾外侧巢状皮质中的神经元也能够分类呈现感知信息(如长短和数字)、根据需要以不同的时间顺序呈现刺激(前瞻性或回顾性),乃至编码执行功能(executive functions,一系列管理和控制注意力等抽象认知功能的能力)和感觉意识。
因此,鸟类的尾外侧巢状皮质拥有与哺乳动物前额皮质相似的强大功能,从而允许它们统筹和安排复杂的认知过程,表现出“聪明”的行为能力。
四、鸟儿会有工作记忆吗?
工作记忆(working memory)指的是将信息储存在记忆中以进行实时处理的能力。拥有工作记忆是一切认知能力的核心,也是前额皮质的一项重要功能。脑损伤、药理和神经生理学等多项研究表明,鸟类的尾外侧巢状皮质也参与了鸟类的工作记忆。
例如,单细胞记录方法在尾外侧巢状皮质中观察到了与哺乳动物前额皮质中类似的“延迟活动”(delay activity)。延迟活动是在施加外部刺激和采取后续行动的时间间隔内,前额皮质神经元保持活跃的现象[8]。
在鸟类中观察到延迟活动,意味着它们确实具有工作记忆这一认知能力的基础。不仅是单个神经元,在由多个神经元细胞活动叠加而成的局部电场位(local field potentials)中,也观察到了鸟类与哺乳动物相似的神经生理活动。这些证据表明,尽管缺乏新皮质那样的分层结构,鸟类的认知活动也能产生与哺乳动物类似的神经生理学指纹。
有关工作记忆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单细胞和局部脑区层面,而对于睡眠与梦境的研究则能在全脑层面提供有关鸟类认知能力的证据。在一项对鸽子的快速眼动睡眠(一种与梦境紧密相关的睡眠状态)实验里,研究人员采用功能核磁共振扫描了鸽子的大脑活动。他们发现,与人类相似,鸽子的大脑在快速眼动睡眠期间激活了边缘系统和前运动脑区,以及视觉和多模态大脑皮层区域[9]。
尽管目前尚无法根据这些大脑活动还原梦境的内容,研究者们依然猜想,鸽子们或许梦到了在飞行过程中躲避障碍物的场景。这些证据初步表明,鸟类的认知过程和哺乳动物一样,与广泛的神经网络活动息息相关。
除了相似之处,鸟类认知的神经生理基础也有与哺乳动物南辕北辙的地方。例如,睡眠研究显示,鸟类并不会像哺乳动物那样在睡眠过程中激活海马体以巩固记忆。它们究竟如何保持和提取长期记忆,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五、鸟类为什么这么聪明?
在这篇最新的Trends in Cognitive Sciences观点文章中,作者们由“鸟类为什么这么聪明”这一问题出发,对“智慧大脑”的构成进行了探讨。那么,什么样的大脑能够发展出智慧呢?
首先,并不是越大的脑袋越聪明。大脑内部神经元的数量、种类和互相之间的联结方式或许更为重要。与哺乳动物不同,鸟类大脑中高密度、大数量的大脑皮质神经元和联络神经元允许鸟类在有限的大脑尺寸中发展出智慧。
其次,哺乳动物所特有的新皮质并不是智慧的必要前提。鸟类的背侧脑室嵴与哺乳动物的新皮质在进化上并不同源,生理结构和信息处理路线上也不尽相同。但背侧脑室嵴与新皮质一样,负责包括感知、运动和联络脑区的信息处理,令鸟类拥有了发展出智慧的可能。这说明,新皮质只是发展出智慧的“充分不必要条件”。
第三,鸟类的尾外侧巢状皮质拥有密集的多巴胺能神经元联结,并参与了几乎所有的认知过程。尾外侧巢状皮质与哺乳动物的前额皮质在功能上极为相似,负责整合信息、编码抽象认知和统筹行动。由于二者在进化上并不同源,这可能是趋同进化的结果。同时也表明,一个类似前额皮质的“控制中心”对于复杂认知能力的发展是极为重要的。
最后,有关鸟类工作记忆和睡眠梦境的研究显示,尽管缺乏类似的大脑结构,鸟类认知的神经生理学指纹与哺乳动物极为相似。这说明在产生智慧的过程中,神经元与神经网络的合作机制可能有本质上的、难以替代的共同点。
至此,我们以鸟类为例,打破了“哺乳动物才有智慧”的垄断观念,从神经元的数量和种类、大脑结构、大脑功能和神经生理活动层面讨论了“智慧大脑”的更多可能。当然,这些仅仅是目前研究比较丰富的方向,还有其他的“潜力股”等待人类的研究和发现。
哺乳动物并不是地球上独一无二的智慧生物,对鸟类大脑的研究将带给我们不一样的视角。探询“鸟类为什么这么聪明”的同时,人类也在探索自身的智慧与边界,向着生命——或者说“生灵”——的本质提出疑问与思考。
参考文献:
[1] Dicke, U., & Roth, G. (2016). Neuronal factors determining high intelligence. 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Society B: Biological Sciences, 371(1685), 20150180. https://doi.org/10.1098/rstb.2015.0180
[2] Klump, B. C., Martin, J. M., Wild, S., Hörsch, J. K., Major, R. E., & Aplin, L. M. (2021). Innovation and geographic spread of a complex foraging culture in an urban parrot. Science, 373(6553), 456–460. https://doi.org/10.1126/science.abe7808
[3] Lambert, M. L., Jacobs, I., Osvath, M., & von Bayern, A. M. P. (2019). Birds of a feather? Parrot and corvid cognition compared. Behaviour, 156(5/8), 505–594. https://www.jstor.org/stable/26737865
[4] Mehlhorn, J., Hunt, G. R., Gray, R. D., Rehkämper, G., & Güntürkün, O. (2010). Tool-Making New Caledonian Crows Have Large Associative Brain Areas. Brain, Behavior and Evolution, 75(1), 63–70. https://doi.org/10.1159/000295151
[5] Olkowicz, S., Kocourek, M., Lučan, R. K., Porteš, M., Fitch, W. T., Herculano-Houzel, S., & Němec, P. (2016). Birds have primate-like numbers of neurons in the forebrain.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13(26), 7255–7260. https://doi.org/10.1073/pnas.1517131113
[6] Güntürkün, O., Pusch, R., & Rose, J. (2023). Why birds are smart. Trends in Cognitive Sciences. https://doi.org/10.1016/j.tics.2023.11.002
[7] Pika, S., Sima, M. J., Blum, C. R., Herrmann, E., & Mundry, R. (2020). Ravens parallel great apes in physical and social cognitive skills. Scientific Reports, 10(1). https://doi.org/10.1038/s41598-020-77060-8
[8] Sreenivasan, K. K., & D’Esposito, M. (2019). The what, where and how of delay activity. Nature Reviews Neuroscience, 20(8), 466–481. https://doi.org/10.1038/s41583-019-0176-7
[9] Ungurean, G., Behroozi, M., Böger, L., Helluy, X., Libourel, P.-A., Güntürkün, O., & Rattenborg, N. C. (2023). Wide-spread brain activation and reduced CSF flow during avian REM sleep. Nature Communications, 14(1), 3259. https://doi.org/10.1038/s41467-023-38669-1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追问nextquestion (ID:gh_2414d982daee),作者:陈硕,编辑:存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