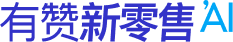作者 | 浩然
来源 | 商隐社
“单身税”是怎么回事?
最近,邻国日本的网友在讨论一个叫“单身税”的话题。
其实早在2017年和2019年,日本网络就曾被“单身税”这个词刷了屏,网友骂到最后才发现,这从一开始就是一条以讹传讹的谣言。
税收关乎国计民生,真实的征税远不会如此鲁莽和草率。
这次的“单身税”又是怎么回事呢?
仔细看下来,所谓的“单身税”不是只有未婚未育的人才交,真实的政策更复杂一些。
前段时间日本政府提出修正案,作为应对少子化的财政资源,将从2026年起,在公共医疗保险之外根据职工年收入每月征收 “儿童保育支援基金”,所有需要交健康保险的人都会再多交一笔钱,用来补贴有孩子的家庭,从而鼓励生育。
这笔钱交多少呢?
日本政府计划到2028年,确保每年少子化财政资源达3.6万亿日元(约合人民币1665亿元),其中1万亿日元(约合人民币462亿元)将通过该支援基金提供。
具体到打工人,日本政府按照2021年劳动者实际总收入进行了估算,征收金额将随年份提高。预计到2028年,个人年收入达20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9.3万元),每月需缴纳350日元(约合人民币16元);个人年收入达40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18.5万元),每月需缴纳650日元(约合人民币30元),以此类推。

日本儿童政策大臣加藤鲇子谈到,这些资金可以使一个孩子在长到18岁前累计领到大约146万日元(约合人民币6.8万元)的儿童津贴和服务费。
4月19日,众议院通过了包含“儿童保育支援基金”在内的《儿童保育支援法修订案》,并送交参议院,如果最终通过,将从2026年开始实行。
虽然为此交的钱没有太多,比如年入1000万日元的人2026年每月要交1000日元。换算成人民币就是,年入46万的人每年交550多块。
但这依然引发了日本民众的一片反对声。日本共同社前不久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超60%的受访者对此表示反对。
即便这不是字面意义上的“单身税”,很多日本年轻网友也认为这项制度并不公平,“最后的受益者只有育儿家庭,而单身青年、没有孩子的家庭或者孩子已经成年的家庭只有负担没有受益”。
更多日本网友的不满在于,这样的举措似乎对于缓解日本的少子化(指生育率下降,造成幼年人口逐渐减少的现象)困境作用不大。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曾在去年表示“接下来6到7年是扭转出生率下滑局面的最后机会。”他还提出用“翻倍的预算”来实施“前所未有的少子化对策”,此次“儿童保育支援基金”的设立也是其对策中的核心措施。
日本从上世纪90年代就察觉到了少子化问题,之后也一直在采取措施,但30多年过去了,几乎没有产生多少效果。
日本厚生劳动省公布的最新人口动态统计显示,日本2023年出生人口为75.86万,总和生育率降至1.2,连续八年下降至历史最低水准。
总和生育率是人口学中特有的一个概念,大致可以理解为平均每个妇女一生的生育子女数量。生育率要达到2.1才能维持每代人口不变。为什么这个数字不是不是2而是2.1呢?因为考虑到了一部分孩子未到成年就会夭折,所以生育率要达到2.1而不是2。
根据去年日本国立社会保障和人口问题研究所的预测,日本预计要到2035年全年出生人口才会低于76万人。
但事实就是,去年日本出生人口已经击穿76万人,比预计到来的年份整整提前了10年多!
所以很多日本民众才不太看好最新的人口对策,在很多民众和学者看来,“前所未来的少子化对策”也只是翻倍扩充儿童补贴规模,收效依然难说。
更重要的是,日本的少子化困局只是加大补贴就能解决的吗?
正如部分日本网友所认为的,“育儿固然重要,但希望政府首先能以建立一个让年轻人在结婚、生育方面持积极乐观态度的社会为目标。”

“少子化最大的原因是结婚率低下,收入越高,结婚率才能越高,而且正规雇佣的员工比非正规雇佣的员工结婚率要高。也就是说,稳定地增加国民收入,创建一个能够让国民安心结婚的环境才是有效的少子化对策。结果政府却要给年轻家庭增加育儿支援金的负担,这完全是本末倒置。”

少子化的背后显然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性问题。
应对30年,为何收效不大?
日本早在1990年就对少子化有了一定认识。这一年,日本发布了前一年的总和生育率,只有1.57。
这一前所未见的数字让日本社会大为震惊,引起了广泛讨论,被媒体称为“1.57冲击”。
对此,经济企划厅在1992年发布了《国民生活白皮书》,其副标题是“少子社会的到来,其影响和对策”,由此,“少子化”这一词语开始广为人知。
在《国民生活白皮书》中,日本企划厅已经表达了少子化带来的劳动力不足和内需不足的担忧,正确预测到了二三十年后将由此出现的一系列社会及经济问题。
然而,日本在7年后才缓慢地推出了少子化对策的基本方针,又过了几年,在2003年才有了《少子化社会对策基本法》。
行动跟认识整整间隔了几乎10年。
日本著名人口学家山田昌弘研究少子化问题长达20多年,他在《低生育陷阱》里谈到了10年延误的原因。
当时正值人口规模较大的“团块二世时代”(日本的“团块世代”指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出现的第一次婴儿潮时期,而“团块二世时代”所代表的第二次婴儿潮时期则指的是1970—1974年)的结婚及育儿期,庞大育儿人群加持下,即便总和生育率下降,但出生的总人口并没怎么减少。
1990年的总和生育率为1.54,而2000年则降至1.36。不过,其间出生人口数几乎没有减少,1990年为122万人,2000年为119万人。
这种“表面的正常”其实淡化了政策负责人的危机意识。再加上期间日本遭遇经济泡沫破灭和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看似威胁不大的人口问题自然排在了极为次要的位置。
从发现问题,到着手解决问题,晚了10年。
但即便如此,日本解决少子化问题也已有近20年,为什么效果微弱?——2005年日本总和生育率达到历史最低点1.26后,曾有微弱缓解,到2015年达到1.45,之后8年又一路下滑至最新的1.2。
与之相比,最早因少子化问题而开始鼓励生育的法国、瑞典等这几年的总和生育率维持在1.8左右,起步较晚的德国也在1.5左右。当然,这些欧洲国家也有移民因素在里面。即便不考虑移民因素,这些国家的效果也好于日本。
山田昌弘认为这20年里日本又犯了一个错误:照搬欧洲经验。
由于欧洲国家的少子化问题出现得更早,且像法国、瑞典、荷兰等的应对策略一定程度上奏效了,法国2010年的总和生育率一度出现了2.03的小高峰。
所以这三个国家经常在日本研究人员的论文、政府的白皮书和图书中被广泛提及、研究,甚至成为日本制定少子化对策的参考模型。
其问题在于,这些国家应对少子化的举措是以本国国情和价值意识为前提,直接套用就会不适配。
比如对于欧美家庭来说,孩子一旦成人,就意味着父母的养育任务结束了,孩子也普遍有离开父母独立生活的习惯。
但在日本,父母不但要把孩子养育成人,还要为他们规避掉所有可能会吃苦的风险,其实在整个东亚社会都是这样,父母对孩子的强烈责任是无穷尽的。
最直观的就是卷教育,这是确保下一代出人头地,有较为优渥生活的直接途径。
以中日韩为代表的亚洲国家国内的各种升学考试竞争都相当激烈,父母不仅要平时要花很多时间辅导、督促孩子做功课,假期也要让孩子参加各种补习班。
曾经被媒体广泛报道的“虎妈”蔡美儿,是一位美籍华人,因用中国传统方式抚养孩子而闻名,对她的两个女儿要求极为严苛,甚至一度让西方世界震惊,虽然她的两个女儿都被培养的相当优秀,但蔡美儿也被人称为“地球上最糟糕的母亲”。
育儿方式可能千差万别,但花费大量时间来卷教育,无疑很难有足够的精力抚养更多孩子。
此外,日本年轻人的自立意识都比较薄弱,甚至很多人认为未婚女子从父母身边离开而独自生活都是不好的。
日本《第15次出生动向基本调查》显示,日本18—34岁的未婚者约有75%与父母同住。即便他们自己收入不佳,但由于父母提供了基本的生活条件,所以也能过上还不错的生活,他们日常基本生活可以靠父母,而自己的收入能作为“零花钱”来消费,催生了日本庞大的“单身寄居族”。
“寄居”其实跟经济大环境的低迷有很大关联,高速发展时期的日本,企业在人事方面普遍推行终生雇佣为基础的“年功序列制”,即人员的晋升和选拔主要围绕着年龄与工龄进行。
但当日本经济走入下行,曾经奉行“终生雇佣”的企业无法进行裁员,为了节约开支,只能用兼职工、临时工和有明确劳动期限的合同工(三者都被称为“非正规雇佣”)。
与之相对应的是,企业内部晋升放缓,管理要职普遍被中老年人占据,年轻人职场的发展空间被大幅度压缩,能找到一份正式雇佣的工作已实属不易,财富积累速度更是不能与父辈相比。
离开“寄居”就意味着要找个同样面对很大不确定性的伴侣,承受很高的结婚和育儿风险,进一步减低了日本青年的结婚意愿,更遑论生育。

图源:日剧《0.5的男人》
所以,成长于日本高速增长时期的人口政策制定者们普遍认为年轻人只是会推迟结婚、晚婚,却没承想年轻人在悄然选择不婚。
日本国立社会保障与人口问题研究所在2023年公布的《现代日本的结婚与生育》报告书显示,在18—34岁未婚青年中,近七成受访青年没有交往对象,其中每3人中就有1人不想谈恋爱。
同样,打算“终身不婚”的比例持续上升,在此次调查中,男性约占17%,女性约占15%,比2015年的同类调查分别高出5个和7个百分点。
“从中流跌落的不安”
山田昌弘把日本青年的种种境况概括为“从中流跌落的不安”,即人们有很强的意识去规避从“普通生活”跌落的可能性。导致人们不愿意结婚,甚至不愿意与异性交往。而且,即使结了婚,这种不安意识也会成为一种妨碍,阻碍人们生育超出期望的更多的孩子。
他认为这是日本少子化的根本原因。
在1955年至1980年代,日本经济恢复并进入了高速成长期,绝大部分年轻人的职业前景和收入都伴随着蓬勃的日本经济一同起飞。
那几代年轻人的父辈生活条件都很差,甚至很多都是佃农,所以他们很轻易就能比父辈生活得更好,即便养育两三个孩子也觉得有很不错的生活。
跟日本成为亚洲经济增长的奇迹相伴随的是,“中产”的理念和生活方式不断普及。
日本再怎么说也是发达国家,2022年人均GDP高达3.4万美元,日本人所说的“普通生活”其实就是中产生活。
日本经济高速发展时期,“中产”也存在通胀,当时日本有“每个人都是中产阶级”“拥有一亿中产阶级”的神话。
1996年,日本家庭的年收入中位数为550万日元。日本有研究机构按照贫困、低收入、中产和高收入把日本社会划分为四个等级,中产人数能超过60%。
即便日本经过了低迷的30年,中产阶级大幅萎缩,“中产意识”也早已深入人心。
期待值拉满,面对的却是残酷的现实。日本年轻人认为过上中产生活已越来越难。日本NHK电视台2022年的一项调查显示,当被问及“何为中产生活时”(多选),60%的受访者选择了“企业正式员工”“拥有住房”“拥有私家车”等。
单是“成为企业正式员工”相比以前就已没那么容易。
日本人规避风险的意识也较强,日本年轻人并不觉得恋爱是恋爱、结婚是结婚、育儿是育儿、孩子的教育费等孩子长大后再考虑、晚年生活等晚年再考虑,也就是说,他们并不会把这些问题孤立开来看待。
自己容易从“普通生活”跌落,而且也不能为孩子提供“普通生活”,就会动摇人们作为父母的自信。如果一个日本人过不上中流的“普通生活”,就会在亲戚、同事、同学的轻视中,“无脸面对世人”。
山田昌弘把子女和父母生活水准的差异作为标准,将日本年轻人划分为四类,发现积极生育的有三类:父母是中产,但自己能超越父母,成为“中上”层;父母比较贫穷,自己能超越父母一代;父母比较贫穷,自己也一样贫穷,没那么强的“中产意识”。
比如大学升学率和人均收入都处于最低水平的冲绳县,2022年总和生育率最高,达1.70,最低的东京都只有1.04。因为冲绳长期被美军占领,没有参与到轰轰烈烈的工业化进程,通过终身雇用和年功序列制度也没有在此普及,民众在这里的生活水平都差不多,没有什么“中产意识”。
虽然只有“父母是中产,自己无法超越父母”这一类型比较倾向不婚、不育,但由于日本中产阶层曾无比庞大,现阶段不顺意的年轻人又比较多,所以成为了相当多年轻人的选择。
在没那么要强,没那么好面子,父母“责任有限”且社会福利水平不错的欧美,年轻人不会有那么强烈的“从中流跌落的不安”。
欧美国家年轻人也面临着失业、收入低等种种风险,但同居或结婚反而是一种避险方式,欧美女性的职场参与度和平等性都很高,两个人都有工作,可以化解很多不确定性。
经合组织(OECD)的数据显示,2018-2020年43个国家婚外生育占新生儿的比例竟高达41.9%!冰岛、法国、瑞典、丹麦、荷兰都超过了50%。而韩国、日本都在2%左右。
所以,山田昌弘认为日本解决少子化难题首先是减弱年轻人“从中流跌落的不安”。如果只是按照“结婚”“夫妻双职工”“育儿”“教育”等各个生活事件零散地进行的支援,保障新一代的最低生活水平,或许在欧美是有效的,但在日本可能无效。
总结
人口转型是人类遇到的新问题,半个世纪之前世界还在担忧人口爆炸,将其视为人类进步的最大障碍,马尔萨斯对人口悲观的预测还被广泛提及。
但转眼间,人口迅速的衰减就打了众多发达国家、新兴经济体一个措手不及,都没想到少子化和老龄化来的如此之快、如此之猛。与少子化相伴的是,日本65岁以上老年人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达到29.1%,为全球之最。
人口转型是新问题,人类也没有经历过一个完整的转型周期,我们对人口跟社会的关系、跟经济的关系了解都很模糊。所以出现了像日本那样,政策晚来10年,抄欧洲先行者的作业,预测跟现实出现10年偏差的种种情形。
山田昌弘认为日本没有从自身国情和价值意识着手去分析、解决问题。
他是人口问题专家,也是日本政府人口问题的高参,或多或少参与了日本应对少子化问题的进程,他这么透彻的领悟也是对过往的深刻反思。
这也说明了要真正搞懂一件事的底层逻辑并不容易,人口问题是这样,其他问题都是这样。
我们往往高估自己对问题的认识能力,无法条分缕析地看清无数错综复杂的条件(其中每一条单独看都像是原因)及其背后,然后抓到一个近似的条件就认为是原因。
更可怕的是我们会从工具箱中寻找已有的解决方法,要么是以前使用过的历史方法,要么是先行者的方法,尽管这些方法与实际情况并不契合。
但发展阶段、前提条件的不同对应着完全不同的解题思路,思考和处理任何事情或问题的方法还是得实事求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