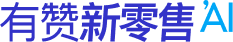保罗·狄拉克(Paul Dirac)常被称为“理论家中的理论家”,他害羞、沉默、似乎缺乏同理心,是科学界典型的孤独者。狄拉克晚年时,有物理学家突然打电话给他,问他是否愿意就其文章里的想法谈谈,他会坚决打断对方并说:“我认为人们应该研究自己的想法”,然后挂断电话。
狄拉克最著名的贡献是发展了量子力学——始于海森伯(Werner Heisenberg)和薛定谔(Erwin Schrödinger)1925年的工作,而当时狄拉克只有23岁。在关于这一理论早期的文章中,狄拉克的论文脱颖而出,就像弗里曼·戴森(Freeman Dyson)所说:“他那些伟大的发现就像精雕细琢的大理石雕塑,一座接一座地从天而降。”[1]
尽管狄拉克作为科学魔术师而广受尊敬,但是许多物理学家——特别是德国柏林和哥廷根的一些物理学家(量子力学的许多基础论文诞生在那里)一一觉得他的语言令人费解,他的论证难以捉摸,还有他的态度冷漠而疏远。爱因斯坦也是那些深感困惑的人之一,“我搞不懂狄拉克。在天才和疯子之间令人炫目的小路上保持平衡,太厉害了。(I have trouble with Dirac. This balancing on the dizzying path between genius and madness is awful.)”玻尔(Niels Bohr)对狄拉克印象深刻,但他也感到困惑,因为狄拉克对于新理论所带来的哲学问题无动于衷,还说狄拉克是“访问过我研究所中的最奇怪的人”。[2]
狄拉克那独一无二的个性以及对待理论物理的态度都源于他在英国西南部最大城市布里斯托的成长经历。据他自己所说,他度过了一个缺爱,没有朋友的悲惨童年,但在科学、数学和工程学方面接受了充分的教育。
在21岁生日8周后,狄拉克来到了剑桥大学开始攻读博士学位——虽然当时他对于现代物理学的了解并不全面,但是他已经拥有电气工程和应用数学两个学士学位。他是一个极其不寻常的学生,一个准备在科学上留下独特印记的局外人,很少有人能猜到,他会注定成为20世纪英国最富成就的学者。
狄拉克后来说,他从未拥有过童年。据他对早年的回忆,他的家庭生活十分痛苦——没人能够幸免,主要是因为他那专断强横的教师父亲,在父亲坚持下,家里几乎不能接待访客,还要求孩子们只能用法语跟他讲话。吃饭的时候,一家人会被分开:狄拉克和他的父亲在前屋,只能用法语交谈,而他的妈妈和兄妹在厨房,只讲英语。
一篇写于1933年的经过详细考察的报道称,狄拉克小时候认为男人和女人说不同的语言。纪律严明的父亲会因细小的语法错误而惩罚他,甚至不让他上厕所。狄拉克回忆说,他认为沉默是避免惩罚的最好方法。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他不愿讲话,除非有很好的理由。
左:狄拉克的母亲佛罗伦斯(Florence)和三个孩子,照片由他的父亲于1909年4月9日拍摄【左一为保罗·狄拉克,此时不到7岁;右一是哥哥菲利克斯(Felix),母亲怀中是妹妹贝蒂(Betty)】。右图(摄于1910年)为狄拉克的父亲查尔斯(Charles),他1866年出生于瑞士,后于1919年10月22日加入英国国籍,自此他的孩子也成为英国公民,而之前保罗·狄拉克的官方国籍是瑞士。图片来源:Courtesy of Florida State University, Paul A. M. Dirac Collection.
狄拉克在小学时就表现不错,但算不上非常特别——他的一个同学是阿奇·利奇(Archie Leach),成了后来著名演员加里·格兰特(Cary Grant)。狄拉克升入高中后就开始崭露头角了。那时正值一战期间,许多男孩都去参加武装部队,而他们留下的尖子班的空缺得以让像狄拉克这样聪明的学生迅速取得进步。这所高中给狄拉克提供了一流的实践教育,允许他不学拉丁语、希腊语和其他不太可能对找工作有用的科目。他几乎每门课都非常优秀,尤其是在数学、科学和技术制图方面。
在十几岁的时候,狄拉克就已经远远领先于班上的其他同学,并且开始思考空间和时间的本质,尽管那时他对相对论还一无所知。同学们觉得他性格古怪、孤僻;有人形容他是“一个身材瘦高,穿着灯笼裤,留着卷发而不像英国人的男孩”。狄拉克的数学老师,因为不能布置出能让他一直专注的作业而感到绝望,于是决定邀请狄拉克学习黎曼几何,而后者欣然接受了邀请。
在狄拉克16岁的时候,他准备去上大学,由于并不明确自己要学什么专业,他决定加入哥哥的行列,去读布里斯托大学读工程学。狄拉克孜孜不倦地研究理论工作,但是他在实验室中却表现出无可救药般的笨拙,大部分的下午时间狄拉克都在焊接电路、操作车床、测量横梁载荷或忙于其他学生工程师必备的技能。
奔涌的思想
尽管很忙碌,但是狄拉克仍需要一个挑战。果不其然,它在1919年晚些时候出现了,这是在他们一家放弃瑞士国籍成为英国公民后不久,正如狄拉克所说,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突然震惊世界”。当时最新的日食观测数据似乎证明,在描述太阳(引力场)致使光线弯曲方面,爱因斯坦的理论要优于牛顿理论——他和他的同学们对这一则轰动性的新闻感到非常的兴奋。(参见Daniel Kennefick于2009年3月在Physics Today发表的文章)
但对于狄拉克来说,他很难找到这个大新闻背后蕴含的东西,关于理论的细节很少,大部分关于爱因斯坦工作的小册子都没什么实质内容、会误导人,甚至经常是错误的。
当参加了哲学家查理·布罗德(Charlie Broad)开设的一门关于科学思想的课程后,狄拉克想了解更多细节的愿望得到了满足,因为课程重点介绍了爱因斯坦的狭义和广义相对论。布罗德曾在剑桥接受过自然哲学训练,他在总结新思想方面很有天赋,总能精确并生动地表达出来。(他会把精心准备的讲义中的每句话读两遍,里面的笑话他会读三遍。)用数学形式表达,由此能够猜测自然定律,这一基本思想方式深深吸引了狄拉克的想象力。在17岁的时候,他踏上了成为理论物理学家的道路。
1921年7月,狄拉克获得一等荣誉学位,但很快他也得到了一份“失业证书”。当时英国经济不景气,就业机会稀缺,狄拉克参加了几次面试,最后都不了了之。一位他在工程系的讲师大卫·罗伯特森(David Robertson)主动为他安排了免费的大学数学课程,并跳过了第一学年。在他的纯粹数学学习期间,狄拉克听了皮特·弗雷泽(Peter Fraser)的课程。
弗雷泽一生从未写过一篇研究论文,却是一位非凡的老师——狄拉克后来说,这是他遇到过最好的老师。弗雷泽热衷于射影几何——研究在特殊变换下不变的几何性质,这是一门与几何绘图密切相关的学科,狄拉克一直研究了近十年。虽然关于纯数学的讲座是狄拉克的最爱,但他把大部分时间花在了应用数学课程上,用牛顿力学解决了很多问题。他也参加了几次关于相对论的讲座,他可能比讲者懂得更多。
当狄拉克于1923年10月来到剑桥攻读博士学位时,校方知道他们迎来了一个不同寻常的学生。布里斯托的一位“智力星探”在他的一份报告中说:“(狄拉克)有点笨手笨脚,喜欢坐着思考,简直是一个隐士,不爱开玩笑,并且经济上十分拮据。”
狄拉克在入学考试中的优异表现给学校留下深刻的印象,学校迫切地想要给他一个研究生名额(他原本都没有资格参加本科生课程,因为他既没学过拉丁语也没学过希腊语。)虽然在知识方面还有很大欠缺,甚至没学过麦克斯韦方程,但狄拉克在数学方面显示出过人的天赋,并有着一位训练有素的工程师所必备的专业技能和鉴别力。
狄拉克本来想从相对论开始他的研究生涯,所以当他被告知导师是统计力学和量子理论专家的拉尔夫·福勒(Ralph Fowler)时,他感到很失望。然而,狄拉克很快意识到,他拥有的是剑桥最好的导师之一——一位人脉广泛、善于鼓励、有能力发现能驾驭的问题的人。
狄拉克迅速而富有想象力地解决了福勒提出的问题,从而确立了自己一流学生的地位。他还在业余时间继续研究射影几何,并寻找各种经典理论的相对论版本来满足他对狭义相对论的胃口。
从他给家里写的那些极为简洁的明信片上,我们可以看出狄拉克似乎心满意足。但是在1925年的春天,当听到他哥哥服下氰化钾自杀的消息后,狄拉克遭受了极其严重的打击,尽管当时他们兄弟俩已经疏远了。
狄拉克对这次悲剧的最初反应并没有被记录下来,这件事一直是个痛苦难言的话题,他和妻子都不愿多言。但他也确实和亲密的朋友谈过,他把哥哥的死归咎于他们恃强凌弱的父亲。此后一段时间狄拉克的效率急剧下降,直到那年夏天回到布里斯托,他几个月没有发表任何东西。在假期快要结束时,他收到了一份来信,里面的内容改变了他的一生。
信是福勒寄来的,里面有一篇文章的校样副本,这篇文章现在被认为是海森伯发表的第一篇关于量子力学的文章。[3]起初,狄拉克认为内容太复杂,便将其搁置一旁。但大约两周后,他的注意力被文中几行附带的话吸引了,海森伯指出他的理论有一个明显的缺陷,那就是位置和动量这两个变量不对易,不过他暗示这个问题并非不可克服。
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狄拉克把注意力都放在这句话上,并意识到它蕴含了量子力学的关键。通过类比于经典力学的泊松括号,狄拉克构建了自己版本的量子力学,而泊松括号对确定动力学系统的时间演化起重要作用。他关于这个主题的第一篇论文《量子力学的基本方程》(The Fundamental Equations of Quantum Mechanics)[4],给海森伯、马克斯·玻恩(Max Born)和他们在哥廷根的同事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40年后,海森伯在英国广播公司(BBC)的一次采访中说,当时他们中没有人听说过狄拉克,但猜到他是一流的数学家。
照片摄于1927年狄拉克25岁时,他背后的树出现在照片里可能不是巧合:狄拉克从他的苏联朋友伊戈尔·塔姆(Igor Tamm)那里学了点东西——狄拉克喜欢爬树,还常穿着套装。图片来源:Courtesy of Florida State University, Paul A. M. Dirac Collection.
狄拉克早期关于量子力学的论文以极为深刻的洞察力和优雅的风格著称。其中许多论文至今看起来仍令人耳目一新,极具现代感。1920年代中后期,自然之书似乎在他面前敞开:他发表了一篇又一篇伟大的论文,共同发现量子变换理论和量子场论、色散理论、密度矩阵和空穴理论,并做出其他几项开创性的贡献。学者们对狄拉克有如此之多的真知灼见百思不得其解,但他们并未从狄拉克那里获得太多信息,直到20世纪60年代,狄拉克才开始谈论他的早期工作。
在一次评论中,他打开话匣,说他在最早的论文中使用了射影几何;他之所以没有在论文中提及这些数学知识,部分原因是他认为其他物理学家对此并不熟。1971年,罗杰·彭罗斯(Roger Penrose)在波士顿大学的一次演讲中要求狄拉克解释他在这些论文中是如何使用几何的,狄拉克轻轻地摇了摇头,拒绝了。不过,他还是在1963年的一次采访中,在回顾自己学习工程学时,阐述了他关于δ函数的灵感来源:
当你想到……工程结构,有时你会遇到分布载荷,有时你会遇到在某一点的集中载荷。嗯,本质上是一样的……但在这两种情况下,你用了不同的方程。从根本上讲,要把这两种情况统一起来,某种程度上这就导出了δ函数。
或许在狄拉克创造性爆发中最大的亮点,是他1928年发表的关于电子的方程[5]。这个方程使量子力学和狭义相对论相容,能同时解释粒子的自旋和磁矩。3年后,在他那篇关于磁单极子的开创性论文中,他顺带用这个方程预示了反电子(antielectron)的存在[6]。1931年秋天,在普林斯顿大学的一系列讲座结束时,狄拉克几乎直接预言了存在反电子,不过没有证据表明他鼓励实验家去寻找这种新粒子。1932年8月,加州理工学院的卡尔·安德森(Carl Anderson)首次发表了与电子质量相同但电荷相反的粒子存在的证据,但他没有提到狄拉克的工作。直到几个月后,学界才意识到安德森发现了狄拉克预言的反电子。30年后,狄拉克带着一种奥林匹克式的超然态度(这已成为他的标志)说,他最大的满足感不是来自反电子的发现,而是来自方程的正确性。
这一成功的预言打动了诺贝尔奖委员会,他们一直不愿给量子力学授奖,因为它之前没有获得足够的实验支持。1933年11月,也就是狄拉克成为剑桥大学卢卡斯教授一年多之后,诺贝尔委员会宣布狄拉克与薛定谔一起分享当年的诺贝尔奖,奖金各自一半,并将1932年的诺贝尔奖追溯授予海森伯。狄拉克成为当时最年轻的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译者注:理论方面,实验方面是25岁的劳伦斯·布拉格,William Lawrence Bragg),这个记录直到1957年被李政道打破(只相差几个月)。
反对QED
狄拉克获得诺奖的几周之后,他提出了真空极化的想法,而他的黄金时期也走到了尽头。他不再对量子电动力学(QED)着迷,该理论所预测的许多可观测量是无穷大的,这使计算变得毫无意义,狄拉克对此深感困扰。1936年末,他短暂地将注意力转向了宇宙学,提出了备受争议的大数假说(large-numbers hypothesis)。该假说认为,一些简单的线性方程将宇宙尺度的巨大数字联系了起来(而不是巧合)。
几年后,狄拉克接受了詹姆斯·斯科特(James Scott)的邀请,就他的物理哲学进行演讲。他能接受邀请是相当令人惊讶的,因为狄拉克公开蔑视科学哲学。1963年,他将其描述为“只是一种谈论已经取得的发现的方式”。
但是狄拉克1939年2月在爱丁堡的那场关于“数学和物理之间的关系”的演讲并没有让听众失望,他用浅显平实的语言给出了深刻见解,全程没有使用一个抽象的数学符号。[7]就连他的引言也直截了当:“数学家玩的是自己发明规则的游戏,而物理学家玩的是大自然给出规则的游戏。”
他建议理论物理学家应该追求能最大可能体现数学之美的物理定律。不过,他没有耐心回答一个显然的问题,即客观上什么构成了这种审美品质,“这是一种无法定义的品质,就像艺术中的美不能被定义一样,但研究数学的人不难欣赏它。”狄拉克后来说,他对所谓的数学之美原则的信仰,对他和他的朋友薛定谔来说“就像一种宗教”。
在狄拉克研究方向改变的同时,他的个人生活也发生了一些重要事件。1936年6月,狄拉克的父亲去世了,直到他生命的尽头,狄拉克都在他的掌控之下。葬礼结束后,狄拉克松了一口气:“我现在感觉自由多了;我觉得我现在是自己的主人了。”
他把这些话写给了他的密友玛吉特·巴拉兹(Margit Balázs),她是他的匈牙利朋友和同事尤金·维格纳(Eugene Winer)的妹妹(当时已离婚)。不到六个月的时间,她就与狄拉克结婚了。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结合,因为她在许多方面都与狄拉克截然相反——健谈、合群、固执己见。
然而,这段婚姻还不错,他们生了两个女儿,他们共同度过了近50年。狄拉克自诩为居家男人,热衷于打理花园和草坪,但也仍致力于理论物理研究,只是与主流学界越来越疏远了。二战期间,他曾担任英国秘密研究核武器小组的顾问,并将部分时间用于发展他提出的想法:用无活动部件的仪器分离同位素。而且他并未完全放弃理论物理研究。他是战争中少数几个还在继续研究QED的人之一,并与他的避难者同事薛定谔和泡利(Wolfgang Pauli)保持着联系。
玛吉特·巴拉兹(Margit Balázs)是理论物理学家尤金·维格纳的妹妹。照片摄于1932年,这是她在普林斯顿的一家餐厅第一次遇见狄拉克的两年前。1937年1月他们在伦敦结婚。图片来源:Courtesy of Florida State University, Paul A. M. Dirac Collection.
20世纪50年代早期,下一代理论家——特别是戴森、费曼(Richard Feynman)、施温格(Julian Schwinger)和朝永振一郎(Shinichiro Tomonaga)——发展了一套更为完备的QED理论,通过重整化系统地消除了麻烦的无穷大问题,理论与实验也非常吻合。但狄拉克却不为所动。当戴森询问他关于新理论有何看法时,狄拉克直言不讳地说,“如果这些新想法不是那么丑陋的话,我可能会认为它们是对的。”
狄拉克认为,在更好地理解光子和电子之间的相互作用之前,试图推动粒子物理学的发展是愚蠢的。由于他几乎忽视了弱相互作用和强相互作用方面的新成果,他逐渐脱离了学术圈,生产力也急剧下降。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当他试图建立引力的量子理论时,他在广义相对论的哈密尔顿形式和束缚态的量子理论方面做了重要工作。这些都是很有分量的贡献,但在大多数狄拉克的同事看来,他只是在他自己的科学死水中挣扎——他是一个值得尊敬的人,但不值得去倾听。
1969年,在从剑桥大学卢卡斯教授的职位上退休两年后,他加入了位于塔拉哈西的佛罗里达州立大学物理系,并周游世界,主要就他的物理学哲学方法发表演讲;他不厌其烦地指出他所认为的QED的致命缺点,并敦促年轻的同事们发展一种革命性的理论,以取代这个他共同发现的理论。
在1980年的演讲“工程师和物理学家”中,狄拉克阐明了他为何坚决反对QED。他的观点源于他作为工程师所接受的训练,重整化需要一种任何有自尊的工程师都不会赞同的做法:在一系列近似实际的、可测量的量中忽略无穷项。在狄拉克看来,忽略方程中的无穷大的量是荒谬的。
其他工程师可能会采取更实际的方法——它能否行之有效,与实验吻合,从而接受这个理论。然而狄拉克不能接受这一点,因为他是不同凡响的工程师——一个有着杰出纯粹数学家情怀的工程师。
他说:“工程师的主要问题是决定做出哪些近似。”一名优秀的工程师会对可忽略项明智地、通常是凭直觉做出选择。“被忽略的项必须很小,而且不能对结果产生太大影响。他绝不能忽视那些不小的量。”
1927年春天,马克斯·玻恩和他的年轻同事们在他哥廷根家的后花园。狄拉克目不转睛地读着报纸,他在德国结识的朋友奥本海默(J. Robert Oppenheimer)也在这里(左四)。图片来源:Courtesy of Florida State University, Paul A. M. Dirac Collection.
坚持原则与古怪并存
就像伟大的诗歌一样,狄拉克的论文值得反复阅读。研究人员一次又一次地发现,狄拉克论文中的思想和见解在首次发表时几乎没有什么影响。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他1939年关于数学和物理关系的论文,这篇论文至今仍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IAS)的理论物理学家之间流传。其中的一位,内森·塞伯格(Nathan Seiberg)告诉我,“如果正文前的日期不是1939年,而是2009年,这篇文论也会同样令人印象深刻。”
在一段特别引人注目的章节中,狄拉克推测出宇宙最初的条件——甚至那是在1939年,他就接受了始于他的学生弗雷德·霍伊尔(Fred Hoyle)的理论,即后来所说的大爆炸。狄拉克指出,如果宇宙仅仅遵循一组给定的初始条件平凡的运动方程,那么它不可能解释地球丰富多样的生命形式乃至宇宙本身所显示的复杂性。而他认为,量子力学可以将这种复杂性归因于宇宙极早期的量子跃迁。狄拉克似乎已经知道他偶然发现了一个重要的洞见,他非常特别地以斜体字总结了出来:
“量子跃迁现在成为自然现象中不可计算的部分,以取代旧机械论观点中的初始条件。”(The quantum jumps now form the uncalcu-lable part ofnatural phenomena, to replace the initial conditions ofthe old mechanistic view.)
塞伯格在IAS的同事尼玛·阿卡尼-哈米德(Nima Arkani-Hamed)对我说:“这是一个惊人的见解。虽然狄拉克不知道宇宙演化的细节,比如现代的暴胀理论,但他对核心概念的理解是完全正确的。所以他有点像达尔文,即使他对内在的遗传学一无所知,他还是能提出自然选择的演化理论。”
阿卡尼-哈米德还强调了狄拉克的论文在技术性上对现代物理学家的价值,包括弦理论家。20世纪70年代初,发展弦理论的年轻一代物理学家意识到他们正在追随狄拉克的脚步。他不仅提出了拓展的物质作为基本粒子的模型,而且在受约束的力学系统的量子化理论中,他还发展出理论学家理解相对论性弦论的量子动力学所需的技术。
20世纪70年代中期,当物理学家们试图理解磁单极子的性质时——这在许多现代基本粒子理论中自然存在,他们发现狄拉克在1931年和1948年的论文中再次为人们设定好了路线[8]。
约1958年狄拉克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他很喜欢干砍树之类的体力活,还帮忙清理研究院附近树林的小路。图片来源:Courtesy of Monica Dirac
狄拉克似乎很少或根本没有关注过早期的弦理论文章,也不理会1970年代物理学家的主流工作,即他们建立的标准模型。对QED的幻想破灭后,他专注于将广义相对论与他的大数假说联系起来。而且他知道许多物理学家认为他是一个坚持原则但古怪的人。尽管狄拉克不为所动,但他有时也会士气低落。毫无疑问,普林斯顿的物理学家约翰·惠勒(John Wheeler)注意到了这一点,在狄拉克80岁寿辰时,惠勒给他写了一封特别贴心的短信:
我写信是想告诉你,我不确定你是否猜到了,许许多多年轻一代和老一辈学者都把你视为追求正直和美的英雄,正确行事的榜样。[9]
狄拉克将这封信存放在他的桌子里。不到两年后,1984年10月20日,他因心力衰竭在塔拉哈西的家中逝世,他的妻子和护士守在床边。他一直工作到最后,他对物理学的贡献并没有随着他的离世而终结。像所有真正伟大的思想家一样,他在身后仍为世界提供源源不断的创造力。
参考文献:
[1] 除非另有说明,本文参考来源见于G. Farmelo, The Strangest Man: The Hidden Life of Paul Dirac, Mystic of the Atom, Basic Books, New York (2009).
[2] K. Gottfried, http://arxiv.org/abs/quant-ph/0302041v1, p.9.3.
[3] W. Heisenberg, Z. Phys. 33, 879 (1925).
[4] P. A. M. Dirac, Proc. R. Soc. London, Ser. A 109, 642 (1925).
[5] P. A. M. Dirac, Proc. R. Soc. London, Ser. A 117, 610 (1928).
[6] P. A. M. Dirac, Proc. R. Soc. London, Ser. A 133, 60 (1931).
[7] P. A. M. Dirac, Proc. R. Soc. Edinburgh, Sect. A: Math. Phys. Sci. 59, 122(1938-39).
[8] P. A. M. Dirac, Phys. Rev. 74,817 (1948).
[9] I. Wheeler to P A. M. Dirac, 8 August 1982, General Correspondence Paul A. M. Dirac Collection, Paul A. M. Dirac Library Florida State University, Tallahassee.
本文译自Graham Farmelo; Paul Dirac, a man apart. Physics Today 1 November 2009; 62 (11): 46–50. https://doi.org/10.1063/1.3265236.
原文链接:https://pubs.aip.org/physicstoday/article-abstract/62/11/46/400676/Paul-Dirac-a-man-apart-Dirac-practiced-theoretical?redirectedFrom=fulltext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返朴 (ID:fanpu2019),作者:格雷厄姆·法梅洛(Graham Farmelo,理论物理学家、传记作家、科普作家、伦敦自然博物馆资深研究员,作品《量子怪才:保罗狄拉克传》获2010年《洛杉矶时报》科技图书奖、2009年《物理世界》年度图书奖),翻译:下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