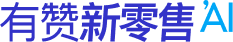从2019年初美国把近百家中国企业列入实体清单,实行高科技出口管制至今,中美科技战持续了近五年并处于不断升级状态。五年来,有关中国如何壮大科技力量的讨论几乎每时每刻都在社会各个角落进行,形成的相关讨论留言、文章、报告、专著可谓汗牛充栋。这也导致光刻机这样的半导体领域核心设备居然成为社会舆论关注的焦点,引来大量的介绍与评论。
五年来,针对中国问题的诊脉发生了明显转向。起初,无论官方、学界还是民间都普遍认为症结出在“基础研究不行”,但在科技战持续两到三年之后,官方文件开始强调“应用创新”的重要价值,民间也有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企业创新才是应对卡脖子的关键所在。为此,赛格大道特约作者余绍清专访了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研究员周城雄,请他来对这一转向背后的原因进行解读。
赛格大道:很多人认为,美国科技强大的根本原因是它的基础研究很发达。对这种观点,您是怎么看的?
周城雄:这是一个认知上的误区。这些年我们很多专家,包括深度影响政策制订的人都受到这个认知的影响,认为美国先是基础研究强大了,然后在技术上领先,然后在产业上强大。这个线性逻辑推导出一个结果,中国搞科研也应该先搞基础研究,再做应用研究,再做试验发展,即推动科技成果转化为产品。从实际层面来看,这种认知已经直接塑造了现有的科研和产业政策。
但是,这个认知跟历史是相违背的。表面看起来,这个逻辑上很通顺,像我们常说的基础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很容易被接受,但实际上,这是一种想象出来的套路。
历史上,美国正好走了另外一条路:先是把经济体量做到世界第一;再是工业产值世界第一;然后才是技术上世界领先;最后才是到科学理论、科学发现方面做到世界领先,也就是所谓的基础研究世界领先。
美国大概在1871年左右已经是GDP世界第一了,在19世纪末已经工业总产值世界第一。在一战前后,美国已经在技术上是世界领先了,涌现出了众多世界级发明家和重大技术发明。但是,到1930年,全球共颁发了90个诺贝尔物理学奖、化学奖和医学奖,其中只有4个颁发给了美国科学家。由于1930年代德国纳粹的大规模迫害,不少欧洲顶尖科学家到了美国,因此三十年代美国获得了10个诺贝尔科学奖项,直到二战之后美国才在所谓的基础研究里领先。
当然我一般不用“基础研究”这个词,我认为“基础研究”这个词不是一个严谨的科学的概念,它没有一个严谨的清晰的科学范畴,更准确的提法应该是理论研究或纯科学研究。
赛格大道:您刚刚提到美国科技力量的实际壮大顺序和我们想象的壮大顺序是相反的,但怎么解释范内瓦·布什主持的报告《科学:无尽的前沿》在中美都得到了很大的关注和重视,在美国社会里,为什么形成了对基础研究格外重视的氛围?
20世纪40年代初期,范内瓦·布什是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的首席科学顾问,组织和领导了制造第一颗原子弹的“曼哈顿计划”
周城雄:美国对基础研究的强调有特殊的历史背景原因:第一个是利益方面的原因。美国在二战之后搞纯科学的人比较多了,很多欧洲的科学家到美国去了。第二个,物理学家在二战当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比如雷达,很多军事技术都是物理学家在发挥作用。
实际上,二战之前的美国是没有科技政策的,甚至没有科技政策这个概念,只存在一些部门对科技研发进行资助,比如农业部。这和西方政府的思维是一致的,因为从牛顿时代开始,政府就认为不应该用纳税人的钱去搞科研,因为议员们普遍认为这是你的个人兴趣爱好,为什么要去支持你呢?个人兴趣爱好就像唱歌、跳舞、弹琴、画画,不可能用公共财政去支持。
所以,在二战之前,美国政府只做了一些公益性的资助,比如地质调查、地理测绘、标准制订等等,但目标也不在于搞科研。
但是二战改变了上述格局。二战中物理学家参与得很深,战争快结束时,罗斯福总统让范内瓦·布什(Vannevar Bush)研究政府与科学家合作的未来形式,这实际上相当于让布什来制定美国的科技政策。因为范内瓦·布什是物理学家出身,二战后期的物理学家不仅在科技领域影响力越来越大,也在政府和社会中扮演关键角色,因此如果能够持续获得政府资助,物理学家的影响力也得以继续保持和壮大。
但布什知道,国会和政府很难答应在非战争时期继续答应庞大的资助计划,于是借用了农业部之前提出的“基础研究”的概念,并提出一个“布什信条”,即基础研究是不以应用为目的的,但是基础研究之后就会带来技术,有一个很好的应用前景。于是,从基础研究到技术进步,再到产业应用,布什搭了一个线性的解释逻辑。
但是,这个报告当时并没有得到美国总统杜鲁门和国会的认可,也就没有发挥出很大作用。后来被重视的原因主要是“冷战”愈演愈烈,特别是1957年苏联率先发射了人造卫星,即“斯普特尼克”时刻,他的报告才真正引起了重视。
1957年10月,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斯普特尼克1号”升空飞行。它的本体是一只用铝合金做成的圆球,直径为58厘米,重近83.6千克
赛格大道:所以它并不是二战之后一下子就成为主流,而是有个长达十多年的积累过程?
周城雄:对。所以像美国的国家科学基金会,也在这个报告之后,大概过了10年才设立。1957年苏联发射卫星的行为,对美国社会舆论冲击很大,舆论影响到政府的决策,所以这之后“布什信条”才真正发挥作用。不过,即便如此,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成立后也没有完全按照布什的报告来。
很多政府部门,比如农业部、能源部、NASA、国防部的负责人都认为,你专门设个部门做基础研究是有问题的,跟我的需求不匹配。所以,美国的基础研究大部分都在政府各个部门支持下进行,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支持的基础研究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只有六分之一左右的份额。
此外,这些部门支持的研究虽然也叫基础研究,但跟布什所说的基础研究是有差异的,布什所定义的基础研究是不考虑任何应用的,自然而然地我这里做出来成果了,你后面就会带来技术。但放在那些部门,它们所谓的基础研究肯定跟这个领域将来的应用是密切关联的。所以实际上美国政府的政策没有完全按照布什的建议来。但是这个报告影响力很大,超出了美国的范围,影响到全世界了,导致全世界其它地方的人、其它地方的国家反倒信了这个报告。
赛格大道:这是一种全球现象吗?比如欧洲、日本、韩国等科技强国也这么认为吗?
周城雄:欧洲还没有完全这么认为,因为欧洲的科学技术传统比美国早,不相信美国是靠基础研究强大才壮大科技产业的。后发的日本、韩国这些国家更容易受这些影响,因为它的科学技术传统比美国更晚。
赛格大道:但实际上,日韩和中国很像,都是先把产业慢慢做大,然后获得比较多的技术突破,像日本从2000年以后才开始连续拿诺奖,这时候日本经济不但腾飞了,甚至都开始下滑了。
周城雄:对。其实在实践中,按照布什的这个报告是行不通的,只能按照美国的历史路径来。但是政策界可以拿布什这个线性模式来说事,影响政策领域、影响决策领域、影响国会拨款、影响政府的行为。
赛格大道: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其实美国以外的后发国家,也有像范内瓦·布什一样的学者,他们希望在政策话语框架里营造一个有利于自己的话语,某种程度上也是为了争夺更多的资源。
周城雄:是的,而且我们的情况还比较特殊,人家用这套话语体系是为了游说国会,特别影响国会、影响民众拨款,因为美国的话语权跟决策权分离的,所以它需要亮起这个武器、亮起这套东西去说服决策、国会拍板的这些人。但在中国,拿这套话语的人群,跟制定科技政策的人群重合度很高,从而造成了认知上的正反馈。
赛格大道:明白了。近代以来,整个人类你说生产力有巨大的发展,肯定是依靠这几次产业革命。但可以确定的是,第一、第二次产业革命和基础研究的关系肯定不那么密切,第三次和现在正在进行的第四次产业革命,基础科研扮演了一个怎样的角色呢?
周城雄:我刚才提过,“基础研究”这个词很难界定。比较清晰能够容易界定一点的就是所谓的“理论研究”跟“应用研究”。如果按照那个逻辑上定义的“基础研究”,我认为那种基础研究很少,而且发挥的作用也不大。几次产业革命也就是技术革命,它跟纯理论或者科学的关系是不大的、关联度不高的;第三次是微电子技术,这跟理论研究是有关联的,量子力学、原子方面的微观世界的这些理论研究是有关联度的。
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说,理论上的突破其实已经完成了。现在我们经历的这次产业革命,其实还在第三次产业革命的过程中继续展开,科学理论上没有什么根本的变化,并没有什么新的像量子力学、相对论这些突破性的理论出来。
比如物理学差不多上百年没有大的理论突破了,你要说这些现代技术的新发展都是靠基础研究作为前提的,逻辑上很难成立。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并不是简单线性关系,斯托克斯(Donald E.Stokes)写过一本《基础科学与技术创新:巴斯德象限》,将研究分为四个象限:
“巴斯德象限(Pasteur’s Quadrant)”,他认为基础与应用是结合的;纯基础研究是波尔象限,就是纯理论的;还有爱迪生象限,是纯应用的;还有一个叫皮特森象限,他的目标既不是想有理论上的突破,也不是想应用,完全是纯粹自由自在的研究,但是他也是在研究。
《基础科学与技术创新:巴斯德象限》于1999年10月由科学出版社出版
像波尔的研究,虽然不以应用为目的,但他的目标是追求有更深的科学认识、有理论突破。皮特森是搞鸟类指南,收集整理各种鸟类的标准,目标也不是理论突破,也不是拿来用,就是他的兴趣,但这个东西也可能对将来的科学发展会有作用。
赛格大道:所以这些象限之间的类别是并立的。
周城雄:这几个象限的研究都会有可能对技术进步是有作用的,不是简单地按照基础研究定义的研究才能推动技术进步。
赛格大道:那么,国家对于研究的态度,比较理想的状态应该是既保持个人自由探索的空间,同时也可以去组织一些针对基础的或是一些偏应用性的研究,这样可以更有利于我们获得突破吧?
周城雄:国家应该大力支持研究,但不要区分什么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因为实际上根本区分不开。
从OECD的统计手册的定义来看,基础研究是不考虑任何应用的,创造新知识的;应用研究是考虑一定的应用,也创造新知识。这两个研究说实话都要创造新知识。但如果我没想过怎么用,我就是基础研究;如果我想着怎么用,那就是应用研究。
赛格大道:这几年,国内有些大企业也在资助科学家做一些研究,比如像腾讯的科学探索奖、阿里的青橙奖,都是资助青年的科学家。此外,大公司的研发投入增长率也超过营收和利润率,怎么看这种现象?
周城雄:科学突破是一个概率问题。像“科学探索奖”这种,出资人是没有目的的,但是拿到这些钱的人可能做应用,也可能做理论,可能他自己都没那么清楚。企业做这个事是很有意义的,为什么?因为科学突破就是概率。
为什么现在全世界各种科技创新速度越来越快呢?
就是因为它不是以前所谓的小科学时代,像牛顿那个时候全凭个人兴趣、全凭私人的资助或者私人的财力在那里做,所有的政府都意识到了搞研究对整个国家发展的重要性,所以它投入的资源多。
投入资源多之后搞科研的人就多了,产生突破的可能性就会大得多,因为所有科学技术的进步都产生新的知识组合,它不是无中生有地创造了全新的知识,任何再复杂的知识都是最基本的知识的组合,只不过组合的复杂程度不一样。
所有有意义的科学技术成果都是产生了有价值的新组合,大部分的新组合可能是没有意义的。产生有意义的新组合这就是个概率问题,一定要产生的新组合足够多,你才会有足够多的有意义的新组合。
所以支持研究的人多,就多产生新组合;产生了新组合,就会更多产生有意义的新组合。所以只要企业多支持、政府也支持、社会其他力量也支持,多支持研究,那么就会有更多的人去做这个事,产生更多的有价值成果。
赛格大道:伟大的创新是不能被计划的,但是支持更多的科学家去进行创新,伟大创新涌现的概率就会增加。
周城雄:是的。这也就是林毅夫跟张维迎的争论,之所以没有争论出结果来,就是因为我认为他们两个人对这一点认识是不够的。二人争论政府要不要产业政策,很大程度上是在讨论政府要不要科技政策。
林毅夫认为,政府要有产业政策,因为需要有基础研究,产业发展要靠基础研究来支持。张维迎认为,政府根本预测不了基础研究成果会在哪、什么时候、由谁做出来,所以你不要有产业政策,不要人为干预,就让市场自由竞争就好。但二人都忽略了科技创新中的概率问题,导致谁也说服不了谁。
赛格大道:在大科学时代,国家的决策变得越来越重要,但从美日韩这样相对欧洲的后发国家来看,他们的崛起首先都是从产业端、应用端开始的。当下的中国,对基础研究的认知几乎成了一种“执念”,那么当前对于企业科研在壮大国家科技力量所起的作用,您怎么看?
周城雄:我们前面说了,创新是个概率问题。对一个国家来说,你参与的人越多,产生新成果的概率就越大。在一个国内,其实是不需要区分政府力量,还是企业力量,还是个人力量,你只要这个国家里面在搞研究的人数量足够多。
假如说一个国家有1000万人在搞科研,一个国家只有1万人。那这1000万人搞科研的,哪怕全是在企业,肯定比10000人全是政府资金支持的人,出现成果的概率要高得多,除非这1000万人水平太低,那可能是不行。如果大家水平差距不大,肯定是1000万人比1000人或者1万人或者10万人出现好成果的概率要大得多。
所以,企业在增强国家科技实力方面,是一个很重要的战略力量,因为国家资源投入是有限的,无论任何一个国家,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是有一定的范围的。典型的就是前苏联,全是国家在投入。当然它的科技实力也很强,但是它为什么在“冷战”跟美国的竞争中失败,它就是投入参与的资源单一,全靠政府,政府能够有全社会的力量大吗?而美国是全社会,除了联邦政府,州政府、企业、私立大学和研究机构、公益基金、个人,各种力量都在投入。
赛格大道:目前中国的R&D,政府投入20%多一点,企业占比接近80%,其中民企投入占整个大盘子的2/3。过去45年里,民营企业的投入规模和比重都在增加,一方面推动中国的科技力量壮大,另一方面也融入了全球的产业链,这使得中国在应对外部压力时,有了更足的底气。这使得相对俄罗斯,我们在反卡脖子方面,反制工具更多。
周城雄:我觉得俄罗斯容易被封杀,主要是它的市场化转型非常失败,企业力量没有起作用,所以虽然它原来的科学技术基础按理说比中国的强、比中国的要好,但因为市场机制建立得很慢,所以企业发挥作用一直是不够的。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联邦政府已经不能控制全国的资源去支持科研,政府的投入也少了,企业发展不充分,市场机制又发挥不够,所以就变得很危险。全世界来看,消费者很难买到俄罗斯生产的产品,可能在军工方面有一点,但在其它领域,现代比较像样的技术产品很难买到俄罗斯生产的。
回到中国的情况,按照统计来说,我们的民营企业所投入的绝大部分,都叫“试验发展”,统计口径上分为基础研究、应用研究、试验发展。企业部分,连应用研究都很少。因为严格按照定义的话,应用研究和基础研究一样,都是要创造新知识,现在企业的研究基本都是试验发展,应用研究占比不到3%。
但是,这个过程是必须要经历的,中国绝大多数知名企业成立的时间都只有二三十年,有的甚至只是10年左右,像华为这种成立快40年,发展情况又比较好的企业,就会很自然走向应用研究,2000年前后涌现的一批互联网企业,像腾讯、阿里、百度成立至今也在25年左右了,他们的科研投入也在进行转型。
我相信,只要我们的市场持续发展壮大,有实力的企业数量多了,就会逐渐从试验发展向基础研究、应用研究迈进,二者在创造新的知识上是一体的,不用做具体区分,让企业自己去判断就好。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赛格大道(ID:saigedashu),作者:周城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