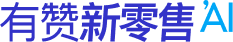在人类学领域,已经有丰富的研究从资本主义批判的角度来思考生殖技术的发展与当代影响,“生物资本”(biocapital)是其中的关键线索。[1]在思考这种以生殖为中心的生物资本主义时,《资本论》中的名句“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无疑成了极具启发的双关语,它既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模式的生动批判,也是关于生殖过程的直白描述。讨论生殖技术的科幻推想与人类学共同说明了这一点。
早在1932年,赫胥黎(Aldous Huxley)就构想了一个依靠特殊生殖技术建立起来的反乌托邦政治经济体。在他的《美丽新世界》中,美国福特汽车公司的创始人福特(Henry Ford)被奉为神明,这不仅因为福特象征着流水线生产技术的规模化,也因为他本人将消费主义视为维护社会和平的关键。
“集体、身份、稳定”是《美丽新世界》中“世界国”的格言,而塑造这样一个静止社会的基础是流水线式的生殖工业:卵子和精子被混合在器皿中并在人造子宫里生长,再以技术手段调整发育环境,批量制造出不同阶层与分工的人类。在这里,人先是作为一种工业产品出厂,接着依照要求工作、消费,不断再生产着这个世界的商品、结构和人。在生殖技术的统治之下,人与商品无异。
美丽新世界,[英] 奥尔德斯·赫胥黎,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7
与《美丽新世界》类似,石黑一雄的《莫失莫忘》也探讨了生殖技术造成的人的商品化。通过女主人公凯西的视角,这部小说讲述了作为生物商品而存在的克隆人的故事:凯西和她的朋友们作为器官移植的原材料被克隆出来,从小在一间与世隔绝的克隆人学校里生活和接受教育,长大后,他们则面临两种身份——或是作为器官捐赠者不断接受移植手术直至死亡,或是(在成为捐赠者之前)作为捐赠者的照护者。
许多评论者称赞这部科幻小说的突出贡献在于赋予克隆人以个性与人性,但我认为这种共情与亲近的写作方式恰恰更残酷地说明了生殖经济中人性不可挽回的失落。《莫失莫忘》的世界设定几乎对应着福柯对国家主权运作形式转变的断言[2]:从旧王权的使死(take life)与任生(let live)转化为现代生命政治中的使生(make life)与任死(let die)。克隆人被赋予生命,只是为了被逐渐杀死,以供养“原生”人类,而他们的商品属性——仅仅出于使用价值而存在和被交换——是这一过程的核心基础。
“Society Must Be Defended” (Michel Foucault Lectures at the Collège de France, 5)
Michel Foucault, Picador 2003
在这个意义上,小说里克隆人进行文艺创作这一细节尤其耐人寻味:凯西与她的爱人汤米听说可以用自己的创作来证明彼此相爱的决心,从而获得延迟最终捐赠(死亡)的机会;但当他们费尽周折找到曾经的校长时,却被告知这只是一个谣言;在失望中,凯西问究竟为什么学校总是鼓励他们进行文艺创作,得到了这样的回答:“我们这么做是为了证明你们有灵魂。”
书里的无数细节当然早已证明石黑一雄的克隆人有灵魂、有感情、有自己的追求与意义,但当生命只是基于使用价值而存在,“我们”与“你们”的区别无法被打破,凯西们没有任何机会摆脱作为“赤裸生命”的次等和临界地位。小说中克隆人的人生既作为生殖技术的想象结果出现在我们面前,也反映了以生殖为核心的生物资本主义世界之中“人”的可能处境。
在《美丽新世界》与《莫失莫忘》的体外生殖想象中,生殖的身体已不存在;然而,人类当下仍以胎生方式繁育后代,生殖的身体及身体劳动仍然应是我们思考生殖资本主义的核心。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的科幻故事《使女的故事》极好地强调了这一点,并血淋淋地呼应了马克思的双关语。
这个故事发生在一个叫作基列共和国的专制统治国家,透过女主角奥芙弗雷德(Offred)的视角来讲述:由于污染和性传染病等因素造成普遍不育,生育能力在基列国被视作重要的资源,有生育力的女性被强制招募为使女,用以保障统治阶级的繁殖。女主角的名字有两层意义,既点明了她相对于大主教弗雷德(Fred)的从属身份(of-Fred),又展示了她作为集权政治的献祭品与受害者的角色(offered)。
使女的故事,[加]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7
正因为推想了女性生殖自由的沦丧,这部成书于1985年的作品被认为精准地刻画了当下现实并启发了学者们的思考。研究印度代孕产业的社会学家潘德(Amrita Pande)就提到自己在博士阶段确定研究选题时,受到了阿特伍德的作品的启发,她的民族志作品Wombs in Labor(《分娩中的子宫》)[3]所描述的代孕者的生活更被认为与“使女”被管理的方式非常相似。
Wombs in Labor, Amrita Pande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4
震惊于阿特伍德的小说的现实性的不只是研究印度代孕的学者,在2022年美国最高法院推翻保护女性堕胎权利的罗诉韦德案之后,《使女的故事》电视剧版女主角在受访时直言“真希望我们生活的世界没有那么像基列共和国”。阿特伍德本人对此事的反应则体现在一张发在社交媒体的照片上,照片里她微笑着举着一个白底黑字的马克杯,上面写着“I told you”(我告诉过你了)。
阅读《美丽新世界》《莫失莫忘》《使女的故事》这样的小说,能让人身临其境地体验到不安与无助,而将之置于人类学关于生命政治与生殖经济的思考中,我们则得以更明确地理解文学推想对现实的批判和预警——科学技术未必有助于人们争取生殖自主权,反而可能成为权力控制的新形式。事实上,科幻作家常常被视为跨越时空的预言者。[4]这种“现实性”源于他们的创作方法——立足当下、抓住历史、承认共时,人类学与科幻共享着这一严肃而紧急的跨时空事业。
人及人性的各种变形是科幻推想最擅长的思辨,何以为人也是人类学永恒的母题。《弗兰肯斯坦》作为科幻历史上的第一部作品,讲述的就是一个“新人类”的故事。在19世纪生物医学技术不断发展的大环境中,雪莱(Mary Shelley)听说了一则关于达尔文实验室的传言——在实验室里可以创造出生命体,于是写作了这部有关人造人的小说。
小说里,男主角弗兰肯斯坦运用科技知识,用尸体拼凑制造了一个丑陋而强大的怪物,又因为害怕对方的样貌,逃避与之接触;怪物在人类社会始终无法获得被尊重与交流的机会,因而要求弗兰肯斯坦再为他制造一个女性同类伴侣;被拒绝后,怪物不断杀害弗兰肯斯坦的亲友并追杀他本人。
雪莱想通过这个故事“讲述我们本性中的神秘、恐惧,并唤醒惊心动魄的恐怖”,她无疑成功了。这个故事被视为关于现代生物学的核心寓言,[5]其影响力尤其体现在有关基因与生殖、赛博格与人工生命的讨论中。《弗兰肯斯坦》代表了自19世纪延续至今的恐惧:关于技术制造的身体,关于人造物与人之间的模糊界限和紧密关联。
毫无疑问,生殖技术的推进与应用必须经过审慎的伦理考察,但是,弗兰肯斯坦的故事不只关乎科技发展,也关乎新的人性。小说里的怪物一次又一次地威胁、祈求着他的创造者给予同情与尊重,却始终被拒绝。“每个人类都对我犯了罪,却唯独把我看成是罪犯”——人造物要求人的承认,要求人对其负责,关于这点,没有什么能比怪物自己说的这句话更切要了。
而在对这个经典故事的不断演绎中,许多科幻作者开始从怪物的主体性出发进行创作。阿特伍德的诗歌“Speeches for Doctor Frankenstein”(《给弗兰肯斯坦的演讲》)就以怪物的口吻对弗兰肯斯坦说,“你已将自己/全变成了我:我是/遗迹,我无知觉”[6]。
我认为阿特伍德想表达的是,当创造者拒绝思考与承认被创造者的人性时,他自己就变成了真正的怪物,而所谓的怪物则成了这一否认和拒绝过程的(不必在场的)标记。当定义人的社会条件不断变化,当对人性的定义本身往往建立在对他者人性的剥夺上时,没有谁可以真正永远符合某种关于“人”的不变范畴;在包括生殖技术在内的科学发展不断挑战人与人造物的森严壁垒时,我们对人和人性的理解也必须被不断反思。
Frankenstein’s Footsteps: Science, Genetics and Popular Culture
Mr. Jon Turney,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8
女权主义哲学家、人类学家哈拉维(Donna J. Haraway)的《赛博格宣言》(A Cyborg Manifesto)是关于这种打破与重造的最富影响力的发声。赛博格(Cyborg)一词是控制论(Cybernetics)与有机体(Organism)的缩写,基于哈拉维的论述,我们可以将之理解为一种介于并混合有机生物与技术机械的生命状态。
之所以要将赛博格视为我们政治想象的资源,是因为西方科学与政治传统始终是关于边界的战争,赛博格不仅可以打破人与非人(有机和非有机形式)之间的种种二元对立,更重要的是可以打破建立这些二元对立并不断加固它们的父权制权力体系。
赛博格还让我们重新审视现实与虚构的关系:我们所在的社会现实总是系于政治建构,解放的可能性就蕴藏在意识到并揭穿这种政治建构中的压迫和不平等,并展开关于新的关系与团结的想象之中。正是在此意义上,哈拉维断言“科幻小说和社会现实之间的界限只不过是幻觉”,科幻作家是“赛博格故事的理论家”。[7]
科幻文学影响了哈拉维的理论建构,而她的研究也启发着科幻创作,另一部关于弗兰肯斯坦的新演绎就是其中一例:杰克逊(Shelley Jackson)在她代表性的超文本小说Patchwork Girl(《拼布女孩》)中“拼凑”出了一个新怪物:原著作者雪莱进入故事之中,创造出了那个怪物想要而未能拥有的女性同类伴侣;但这一次,女怪物不仅与雪莱本人相爱,还前往异国旅行冒险。
在哈拉维更晚近的著作Staying with the Trouble(《与麻烦在一起》)中,她不仅与科幻作家巴特勒合作,还利用了自己的小说来想象一个人们结亲(make kin)而非生殖的世界。
Staying with the Trouble, Donna J. Haraway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6
再回到雪莱的《弗兰肯斯坦》,从赛博格的理论视角重读这个故事,他的悲剧早已注定。这不是因为科技发展必然会造成不可知的恐怖后果,而是因为弗兰肯斯坦们拒绝负责却妄图控制的统治者姿态。负责任地思考技术(尤其是生殖技术),意味着拒绝二分的区隔,拒绝以控制和压迫为出发点的创造,承认科技是我们生命过程的一部分,并认真理解我们已经处于边界、已经被混合这一事实。“做赛博格而不做女神”,这是科幻与人类学共同致以我们的礼物与请求。
在写作“科幻小说中的生殖想象”这两篇文章时,我有意选择最负盛名、影响最为深远的生殖想象文本,以期达到科幻与人类学共读的最佳效果,但无意造成的结果是,本文涉及的绝大多数作家都为女性科幻小说家[8]和女性人类学者。这不是出于偶然或偏见,而是准确反映了创作领域和研究领域的关注形势。
人类学者拉普(Rayna Rapp)对羊膜穿刺技术的讨论或许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这种关于思考的性别分布。在研究中,拉普发现这项产前诊断技术所涉及的主要劳动者(遗传学家、医生、孕妇)往往都是女性。尤其是最初选用这项新技术的怀孕女性,她们被迫置于“道德先驱”(moral pioneer)的困境中,必须在充满未知危险的情况下做出孤独而困难的抉择。
可以说,女性科幻作家与女性人类学者在生殖问题上的率先研究与想象,或许正源于她们共享着直接的身体经验与现实境遇,与拉普所说的先驱性同构。
但是,在承担这种先驱责任的同时,我们必须相信,这些推想与重构本身也是一种具有互助意义的关怀劳动。在苏丹北部某穆斯林村庄的田野生活中,人类学者博迪(Janice Boddy)发现[9],当女性进入生殖关系时,她们也同时进入了Zār(指被邪灵附身以及相关的驱邪活动)的关系,即当地女性往往将生殖相关的身心痛苦归因于邪灵zayran作祟。但是,女巫/医的引导,让被附体的女性可以进入仪式中的迷幻状态(trance)来宣泄与表演。
女巫/医是这个精神世界的重要社会角色,帮助困境中的妇女理解她们的生殖遭遇,并抵制女性在社会生活中被污名与被物化。这让我想到拉普故事里的先驱们,也想到人类学家和科幻小说家。不过,Zār是真的吗?或者,超现实的科幻想象有意义吗?
Wombs and Alien Spirits: Women, Men, and the Zar Cult in Northern Sudan
Janice Boddy,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89
“如果你是个好的讲故事的人,那么谎言比现实更真实;如果你是个糟糕的讲故事的人,那么真相比谎言更糟。”[10]这是人类学者、导演鲁什(Jean Rouch)对电影的看法,我想以此作为本文的结语:因为它抵制了真/假分类本身,而将重点拉回到作为行动的创造(poiesis)。重要的是,思考多重差异,想象另类可能性可以如何生成新的现实。在故事里,在讲故事的手艺活中,“讲故事的人遇见了自己”。好故事隽永。
参考文献与注释
[1] HELMREICH S. Species of Biocapital[J]. Science as Culture, 2008,17(4): 463—78.
[2] FOUCAULT M. Society Must Be Defended: Lectures at the Collège deFrance 1975—1976[M]. New York: Picador, 2003.
[3] PANDE A. Wombs in Labor: Transnational Commercial Surrogacy inIndia[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4.
[4] 除了阿特伍德的著作被屡屡拿来与现实比较, 巴特勒也曾被视为精确预言了特朗普的出现:在她1998年出版的《地球之种》系列的第二部《天赋寓言》里, 一位右翼白人政治家以 “让美国再度伟大”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为宣传口号登上了美国总统的宝座。
[5] TURNEY J. Frankenstein’s Footsteps: Science, Genetics, and PopularCulture[M].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8.
[6] 笔者试译。原文为 “You have transmuted/yourself to me: I am/avestige, I am numb”
[7] HARAWAY D. A Cyborg Manifesto: 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alist-Feminism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M]//Simians, Cyborgs and Women:The Reinvention of Nature. New York: Routledge, 1991: 149-181.
[8] 唯二的男性科幻作家是赫胥黎和石黑一雄, 但如文中提及, 他们对新生殖的构想中不存在 “身体” 。
[9] BODDY J. Wombs and Alien Spirits: Women, Men, and the Zār Cult inNorthern Sudan[M].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89.
[10] 笔者试译。原文为 “If you’re a good storyteller then the lie ismore true than reality, and if you’re a bad one the truth is worse thana half lie” 。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信睿周报 (ID:TheThinker_CITIC),原载于《信睿周报》第107期,作者:叶葳(明尼苏达大学人类学系博士候选人),栏目主理人:朱剑峰(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